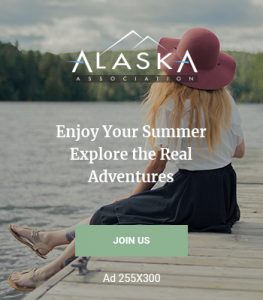文扬
与往年的惯例一样,《求是》杂志2012年第1期再次发表胡锦涛总书记的文章。此文是他在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强国”这个战略的定位,就是公开的国际竞争。
着眼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力量竞争,以此为背景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力量,显然,这正是典型的?#25991;化民族主义?#12290;在学术界,该主义与强调人类普世价值、普世文化的”文化世界主义”相对。
文化民族主义的前生今世
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回顾历史,自清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建国,曾有过一波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
其时,面对”西学”、”西力”的强烈冲击,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文化人,无论是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对于如下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实际上是有共识的:中华大地上的四万万人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首先要将其聚合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再以这个”中华民族”为基础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使民族完成从”文化民族”到”国家民族”的转变,使人民完成从”’天朝子民”到”现代国民”的转变。
百年前这一代文化人都是典型的国学背景,且保留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于是不约而同地看中了通过振兴传统文化来塑造民族精神,继而建立民族国家这样一种政治策略。
梁启超的话:”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章太炎的话:”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反之,”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 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国粹学报》、《民报》)
就这样,以救国和建国为目标,以”国学亡则国家亡”为号召,以民族文化-文化民族-国家民族-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路径为蓝图,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大潮。
但是事与愿违,历史作证,清末民初由中国文化人开启的这一条靠文化民族主义立国的道路,并没有走下去。
回过头来看,无论后来又出现了哪些历史事变,发生了哪些道路转向,总之,1949年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政治民族主义的产物,并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结果。
从世界范围内观之,中国1949年革命的成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压迫民族,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成功。毛泽东和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就是将中国农民群体政治化的成功。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天然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力量,一旦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一旦成为了 ”人民共和国”建国事业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得了。
现代国家建立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历史很无情,人们看到,政治民族主义的胜利,不仅取代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角色,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同时也将这个曾经的革命之子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新中国建国后,随着执政党开始向虚妄的”世界革命”转向,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标志,中国近代史上持续长达百年之久的、由中国文化人物领导的、曾经波澜壮阔的早期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在一片哀鸣声中宣告寿终正寝。
回顾地看,也许,由中国文化人领导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终究承担不了救国和建国的重任;也许,政治民族主义取代文化民族主义,乃至否定文化民族主义,也是历史之必然。毕竟,工农性质的”人民共和国”与国民性质的”民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只能是由文化精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且内在地带有”不准阿Q革命”的傲慢与歧视,最后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仅如此。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假如确实存在着一个主宰着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该逻辑就是:当政治民族主义发现文化民族主义并未真正消亡,正在人民共和国里重建其文化优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一场旨在”灭资兴无”、高高树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彻底粉碎掉”封资修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毛泽东在文革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借尸还魂已显得忍无可忍,他的一个批示是:”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文革” 十年,轰轰烈烈,到结束之时,也就正好实现了当年”国粹派”所最害怕出现、最极力要防止的那个结果,即所谓”国学亡”,或民族文化之亡。
为了国家而从振兴国学着手,最终的结果,却是被自己的国家将国学彻底消灭,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坠入的这一个悲剧性的历史怪圈,举世无双,空前绝后。
在世界近代史中比较,英国和法国是最早实现了各自文化和国家统一结合的两个老牌民族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则是两个从典型的文化民族转型为国家民族的成功范例。在这些范例中,都没有出现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互为对立的情况,恰恰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
文化民族主义在”发展型国家”中的缺位
中国早年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最为担心的,是”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如坠九渊,永远沉伦”。(邓实)
此论并无新奇,在那位讲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先辈龚自珍之时,这就是一个已为中国人所明了的道理。但假如当年这些文化民族主义领袖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西人欲完全西化我中华,是为了亡我国家、灭我种姓,而我中华若要不被西人灭亡,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也必须要使本国完全西化,必须将古老中华改造成一个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新式国家,走上完全和西方一样的强国之路。这个道理是否成立?
如果同意这个道理,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如果中华的西化不得不包含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否定,那么本国文化民族主义也就最终难免要成为本国政治民族主义的牺牲品。不同的只是操刀者,前一个操刀者是西方帝国主义,后一个操刀者是本国工农阶级,结果却是一样,都是要拿中华传统文化和其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开刀。这个结论能否接受?
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实践理性强于认知理性,事情早已做完了,理论还踉踉跄跄地落在后面。众多在自己的”新中国”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的文化人,至死也没能完全明白自己这个满腔热血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为什么就成了”臭老九”,自己这个当年的革命先驱怎么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但现实却是,无论传统文化的境况如何,无论文化民族主义的地位如何,也无论文化人物的集体命运如何,前后两个三十年之后,这个抛弃了自身传统文化的文化新中国,却先后在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跃成为了”发展型国家”最大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国际学界”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中考察,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发展型国家”共同具有的一种发展动力。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将国际社会的生存法则强加到了所有后发国家身上,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有出路,使得这些不甘屈居人后的国家自我激发出了一种以”赶超”为目标的强烈的民族主义。
在政治方面,”发展型国家”按照西方强国的标准规划本国的国家建设,提出国家的权利要求,增强国家的外在权力。在经济方面,”发展型国家”致力于摆脱西方的经济压迫,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国家的实力地位。正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棗政治的和经济的棗为这些 ”赶超”性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战争历史、共产主义的”目标文化”、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府等,也都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这个”社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成功。如查莫斯.约翰逊所认为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是一种准革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们所实施的社会事业的目标的合法性;当经济发展被设定为一个压倒性的目标时,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成了一种革命事业,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实现目标的机制。
从上述这样一个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重要结论:
一、正是以”赶超”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民族主义推动中国走上了”发展型国家”道路,而”发展型国家”的成功归根结底是”西化”的成功。在这条道路上,一个亚洲国家越是成功,就越像是西方国家,就越是远离本国的传统文化,越难以完成自身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内在统一。日本是如此,韩国是如此,中国亦如此。
二、中国在”发展型国家”道路上取得成功,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得益于中国自身的战争历史、共产主义的”目标文化”、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府等因素。然而,非常明显的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以及同样是作为帝国主义时代”刺激-反应”之产物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这个”赶超’事业中实际上是缺位的,不在场的。关于”发展型国家”主要特点的主流观点是:1)持续的发展意愿;2)高效的官僚机构;3)紧密的政商合作;4)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其中并没有诸如”儒家价值观”等传统文化因素这一项。
三、由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也就是”西化”的成功,与东方文化并无太多关系,所以,”发展型国家”的崛起与其说是东方文化的崛起,到不如说是西方文化通过东方国家实现的更大的崛起。
文化民族主义的再次回归
近年来,关于亚洲各成功的经济体越来越类同于西方经济体的观点很盛行,关于中国的崛起能否同时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质疑也很盛行。从西方的角度看,事情很简单:任何一个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而崛起的非西方国家,都是西方国家的翻版,都不太可能实现其非西方传统文化和现代国家的统一。
无一例外,国家越现代,也就意味着越西方,越是与本国传统文化脱节。
要解释这个现象,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并不困难。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西方的一个发明。在此之前,所有的民族都可以说是文化民族,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学、共同的宗教维系在一起,处在一种停滞的、无意识的自然状态中,没有全民族统一的政治历史。当现代民族国家在英法两国首先出现并成熟之后,世界就随之掀起了成立现代国家的浪潮。而在这个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可以说,除了英法这两个民族之外,所有其他民族的现代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被成立”的。也就是说,每个民族在从原初的文化民族向国家民族转型的过程中,那个在本民族中激发出民族自决与民族主权思想的政治历史是外来的,被强加的,或者是以外来思想冲击的形式,或者就是以外国军事入侵、经济入侵的形式。
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现代国家的连续打击下一败再败,面对帝国主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也一一对应地经历了首先自认为器物不如人,继而自认为政制不如人,最后再到自认为是文化不如人这三个阶段。
一个文化民族,到了不得不靠否定自身传统文化来转向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地步,即使最终转型成为了国家民族,建成了现代国家,这个国家不是西方国家的翻版,还可能是什么呢?
就这样,最早的现代国家是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完美结合,最晚的现代国家是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互相否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世界各国分布其上,每一个位置就对应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如此来看,我们这个只能算是”后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整体”文化水平”上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恐怕也已不言自明。
去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对此有这样的表述: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不算太迟,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喧嚣泡沫烟消云散之后,中国人至少是认识到了:在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个大对局中,我们面临的形势比一百七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强不了多少!
一百年前的我们那些可爱的文化民族主义先辈们,即使是无力承担救国、建国的历史重任,但也不至于就被推上祭坛,作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刀下鬼。谋杀了民族文化,也就谋杀了文化民族的立身之本,无论后来变身成了一个什么国家,百年之后还要再来拜谒亡灵,重新还债!
好在,人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极强,复活的速度极快,毕竟,这已经是一个先后经历过不同的炼狱煎熬过的顽强生命,包括当年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和当前经济民族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这个生命能熬到今天,虽遍体鳞伤却仍精神矍铄,恐怕这世上也没有什么还能真的置它于死地了。
近年来,它开始迅速地复活。毫无疑问,在世界舞台上,它还是当年的那个文化民族主义。因为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施行直接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通过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对非西方国家施行的间接控制,仍一如既往。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所说:”(今天的)帝国主义还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
《求是》杂志新年第一期上刊登的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近几天来,这段话在西方媒体中引起了一片热议,评论者大都把此话放在中国共产党时左时右的路线调整,民间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高层领导人的内部斗争,以及十八大布局等现实框架内加以解读,并没有深入地看到这一立场在大历史尺度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当然,对于这些天天忙着说三道四的西方媒体人,要求他们多懂一点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勉为其难了。
人们需要理解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的、后发的”发展型国家”,其民族主义始终是旺盛的,也始终在为国家发展提供着强劲的动力。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典型的民族革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棗哪怕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棗也是一种准革命体制。现在开始的这一场由执政党领导的、以国际竞争为导向的、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文化强国”运动,毋庸置疑,也不会改变其民族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也就是百年前以”欲谋保国,必先保学”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今天的回归和延续。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把胡总书记的这个话换成百年前的文言表达,也就是”欲谋强国,必须强学”。
2012年开年,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为继中国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全民运动,宣告了它的潜龙出渊,凤凰涅槃。
2012年1月7日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