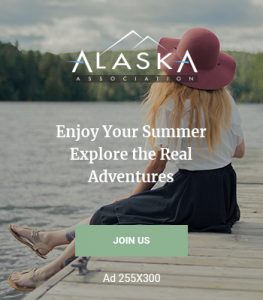王芳已经离开我整整58个年头了。
当夜深人静,或我独自一人走在黄昏的小路上,或对着银色的月光,我都会想起她,五十八年来我和她的点点滴滴都成了我永难忘怀的往事。
我出生在西南边陲一个叫柳镇的地方,虽然山青水秀但三,四十年代的西南,交通僻塞,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电,也没马路,完全是一个原生态的地方。我的爷爷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而我的父母也只生了我一个,这叫一脉单传,因此,我成了四位老人的宝贝。我的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香,蜡纸烛之类的东西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在当时就算是小康人家了。爷爷和父亲都念过私塾,在当地还算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供我上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镇上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学,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坚持让我继续升学,(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要上中学,高中,就必须到离柳镇80多里路远的县城才有一个中学。记得当时十三岁的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挑着一担箩框,箩框一头装着大米(我的学费),另一头放着我的换洗衣物和必要的读本用具,在崎岖的石子摇摇摆摆地走走停停,从早上日出走到夕阳西下终于到了县城,去到舅舅家,舅舅一家也是靠做小生意过活,日子还算殷实,舅舅一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中国人的纯朴善良越在交通不发达,贫穷落后的地方越加显得真诚,我和父亲在舅舅家住了约一周后便去中学报到。我记忆中好像没有经过考试,只是老师口试一番就算考上了,大概因为当时学生来源少的关系吧。用大米交了学费,办好一切手续我便上了中学,上了初中,一种新的完全不同于柳镇的生活开始了。同学中有女生(在我们乡下女孩子是不能上学的),老师们多数是因抗战到大后方来的,他(她)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上课,我对所有一切都感到新奇,从这时起我才知道柳镇外面还有这么大个天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我才知道中国之大,世界之五彩缤纷,我开始做着不同的梦,很羡慕那些从大地方来的老师和同学,他们见过世面,谈吐不凡,回忆那时的我真是青春焕发,斗志昂扬,我尽情地吸引着知识,希望考上外省的大学,走出这四面的大山。直道1946年,当我16岁的时候一件极意外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郦年暑假,父亲提前带来口信,让我务还回家。这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直接升入高中,毕业典礼刚一结束我便匆匆上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脑子里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许许多多的幻想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嘴里哼着喜爱的歌,山是那样绿,水是那样清,天空一片湛蓝,心境开阔而美好,带着欢乐的心情我到了家,进门我就傻了,家里人来人往,都是些亲戚邻居,各自都在忙忙碌碌,看到我都异口同声地大声喊,”德勤回来了,回来了” 我不知他(她)们在干什么,这时我的父母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走到平时我住的房间,只见屋里贴着大红”囍”字,床也变成一张长方型的双人床,挂着漂亮的绿花布帐帘床上是四床绸子被面的被子,还有花枕头之类,我依稀感到什么,但我不能相信,这时父亲说话了,他说:德勤呀!你已经长大了,我们家四个老人要人伺候呀!家里里里外外也要有人打理呀!所以我们给你娶了一门媳妇,虽然比你大了些(大我七岁,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人老实,又能干,家里有了她,我们老的也有靠了,你在外面读书也就安心了,你说是不??在那个年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说什么?只能任人摆布,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唢呐,笛子,二胡,锣鼓,一齐吹吹打打起来,几乎柳镇的乡亲邻里都来贺喜看热闹,中午时分,一乘花轿抬着我那从未见面的大媳妇进了家,接着是拜堂,行大礼,炮竹乒乒乓乓响过不停,我只觉得天昏地暗,让人拉来扯去,像一个木偶,一会是敬酒,一会是磕头,我敬酒,喝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热闹的场面持续到深夜,人们才散尽。我被母亲拽进洞房,只见床上坐着一个头上顶块红布的女人,母亲让我去揭她头上那块红布,我知道这就是父亲对我说的那个”媳妇”,她就是那即将成为我家四个老人依靠的那个人,在母亲一再的催逼下我鼓足十二分的勇气一把抓下那块红布,终于看到了这个人的庐山真面目,她是个高大而粗壮的女人,黑红四方的脸堂,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像是我的”老大姐”,我不敢仔细看她的脸,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我也回忆不起她当时的模样,当我想到自己将和这个”大姐”共度一生时,我全身发颤,两腿一软倒在了床上,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不知道父母亲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总之,当我醒来时已是日高三丈的大白天了,我的那位”大姐”坐在屋子的一角抹眼泪,我坐起身来,头昏昏沉沉的,她见我醒了,急忙去叫来父母亲,二老说了些安慰的话,又跨了他们的儿媳妇几句,便让我起床梳洗,吃饭,我的洞房花烛夜就这样过来了,毫无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第二天一整天仍有客人不断来道贺,我仍然像木偶一样让大人们拉来扯去,到了晚上,我实在太累了,便早早地上床,倒头便睡,半夜醒来发现我旁边躺着那个既陌生又让我生畏的女人,吓得我一动不敢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具僵尸,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我感到自己是在受侮辱,被伤害,我下定决心等天亮就回学校。我已为四位老人娶了媳妇,这场闹剧已经收场,我该走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头也不回的朝县城走去,从此我几乎不再回家,直到很多年以后。
我所谓”结婚”后毅然返回学校(这时我已住进学校的男生宿舍)。情绪低沉极了,同学们知道这件事后,有的为我唏嘘,有的为我不平,也有的认为十六岁的男子汉结婚理所当然,—–我自己则感到茫然,正在这种彷徨无助的时候,一双媚人的大眼睛常常注视着我,投来同情的眼神,她就是这篇文章开始提到的玉芳。
玉芳是这个县城参议长的独生女儿,(参议长相当现在大陆的人大委员长),长得眉清目秀,娇小玲珑,同学们一致认为她是这所中学的校花,玉芳比我低一班,她不但学习成绩优良,还有一付好嗓子,能歌善舞,天真活泼,四十年代的中国,十五岁的女孩就算是成人了,在农村有的都已生儿育女,玉芳的父亲是当地的绅士,又是参议长,对这个独生女特别娇惯,因而她在学校也就显得身份特殊,那时的在校生是男女互相不说话的,玉芳则不然,她大方得体,不管男生女生她都交往,在全校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女生中,她是唯一敢在大庭广众中与男同学说话的一个,她家里藏书很多,她将许多书带到学校让同学看,也因此使大家能读到许多课外书籍,增长了知识,记得巴金所写家春秋三部曲就是就是她借给我看得。到了1948年,我上高二,她上高一,我们的教室紧挨着,18岁的我,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在我的脑子里经常出现玉芳的身影,只要下课,有事没事我都要从她的教室门前经过一趟,从玻璃窗向里看她一眼,有时正赶上她也正朝外看,我们对视一下,我便会一天都感到欣喜,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玉芳每每下课后都会站在教室门口,只要我一出现,她便报以灿烂的笑容,我心里甜甜地,好像有很多话要对她讲,但,我没有勇气,更没有胆量,我们就这样每次对视几秒钟,上午,下午课加在一起,每日也就两分钟,但这仅有的两分钟,却让当时的我回味无穷渐渐地我们越来越多的接触起来,原因是有一天他在教室门口等我,当我出现时她走上前来,将一本鲁迅的”彷徨”送给我,说一声,好好看一看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里面夹了一张小纸条,笔迹娟秀,少少的几个字”为什么这样消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心怦怦地跳过不停,我感到爱情已悄悄地爬上心头,初恋是那样的甜美,那样的激动人心,但只要想到家里的”大姐”我便垂头丧气,不敢面对玉芳了,我只是想躲,就越是想见到她,只是想逃避就越是逃不开,我像巴金小说”家”中觉新一样的感到压抑和无奈,封建婚姻是那样残酷地扼杀了我的感情,我不知所措,我彷徨,徘徊,甚至有几天我躲在教室里不出来,玉芳感到了什么,一天下课后他突然跑到我的教室,对我说:”王德勤,你为什么总躲着我?你怕什么呀!?” 她的大胆,她的直率,在当时那个年代,简直是鹤立鸡群,同学们都被她的举动震惊了,我更是吓得无言以对,直到后来她提起这件事仍然很得意,从此以后同学们几乎都知道玉芳爱上了我,我的几个好友都劝我接受这份爱,我也深知这份感情的珍贵,一方面我矛盾,没有勇气,而另一方面我又沉浸在初恋的甜美中,那时我们仍然不敢公开接触,只是鸿雁传书,通过写信传送着彼此的思念和向往,谈各自的理想和抱负,我也对她坦诚了我的家庭状况,她回信说,我早就知道你已结婚,那不是你的意愿,有什么关系呢?你的那个她其实也是受害者,你对她应该好些。我万万没有想到玉芳会这样看待我这有名无实的婚姻,她的开朗,大度,使我更深的爱着她,我对她的感情像一杯浓浓的美酒,有时我们也会偷偷地避开同学们说几句话,话虽不多但彼此的眼神却传达着相互的深情。记得在一个星期日,同学们都回家了,她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对我说,”我在校门口等你”,不等我回答扭头就跑了,我是多么希望与玉芳单独呆一会呀!但,我家”大姐”的影子又出现在眼前,我感到对不起玉芳,也怕同学们看见。总之,我非常犹豫,最终还是玉芳的真情和自己的真爱战胜了,我头也不回的向校门口跑去,远远地便看见玉芳一人站在那里,我跑上前,她回头给我一个放下了心的微笑,向我点点头径直地往学校后面走去,我们学校后面有一条通往城里的石板小路,路的两侧长满密密的高大的榕树,静静而幽深,我们第一次并排走在一起,谁都不说话,在浓浓的林荫道,在阳光泼洒的路面上,走着两个相爱的沉默的人,谁都不知怎样开口,只有用?#27492;时无声胜有声?#26469;形容当时的情景,最终还是玉芳开口,她说:”德勤,我喜欢你,我什么都不怕,你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不算数,我不在乎,我相信一旦明白了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她会离开你的”我大吃一惊,玉芳的话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过?#22823;姐?#20250;离开我那个家,中国的传统观念禁锢着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和她这种交易式的婚姻太悲哀了,但,我相信,她宁原守活寡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我的家,我将我的想法告诉玉芳,她沉默了,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在静静的小路上走来走去,其实这种时候不需要任何语言就能深知彼此的心意,既是说一两句,那都是从各自的心底流淌出来的,我只感到甜美的温柔,我恍惚脱离了当时我所处的环境。进入瑶池般的境地。这一次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是第一次与玉芳对话,它在我心底埋藏了整整60多年,我现在已是一个耄耋老人,终其一生我都在回味它。
这次心与心的交汇后,我们又恢复到彼此在教室门口交换眼神和信件的情况,这一缎段时间是我和玉芳交往较多的时段,她能歌善舞,每当校庆,国庆—–等等节日,学校的庆祝会上总有她的节目,有一天她忽然在教室门口送给我一个红绒布包,说一声”给你的”就走开了,我打开包一看,是一把锃亮的口琴,这在当时就算是非常新式的乐器了,我高兴极了,从此,我无师自通地不断练习,半年左右,我居然成为全校的口琴演奏员,每次玉芳在台上唱歌,我为她伴奏,那种感觉真是美好极了。
时间飞快,转眼到了高中毕业,我的第一理想是考上大学,这时我的家乡已临近解放(共产党来了),社会秩序很乱,特别玉芳家,她父母整日惶惶不安,她因此而安不下心来,我们偶尔在一起时,都是谈时局,对我们的前途感到茫然,我们只能彼此安慰,她鼓励我一定要考上大学,1950春我的家乡解放,暑假我考上了四川工学院水利系,而玉芳则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首先是她父亲因身为国民党参议长,首当其冲地被管制,因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患脑溢血死亡,接着是她母亲不堪忍受丈夫逝世,家庭巨变的重创投河自尽。当我知道这一切后,我不顾一切地去到她家,当时的环境充满火药味,我们顾不得许多了,我握着她的手,尽量安慰她,她鼓励我要好好将大学上完,并告诉我不管将来如何她要争取上大学,她要等我,我也表示我会一直等她,我俩”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我们在无限依恋的情况下分别了,几天后我去四川,她已离开了生她养她20年的县城去到省城投奔她唯一的亲人姨妈。她姨夫是个中学教员,姨妈作会计工作,有两个女儿,玉芳的到来虽出乎他们的意料,但仍然热情的接纳了她,特别是姨妈对她疼爱有加,玉芳含着悲痛的心情将这一切写信告诉了我,希望我努力学习,不要为她悲伤,接到这封信,我有如万剑穿心,但,学院刚开学,更主要的是我没有路费回乡看望她,在她最困难,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去到她身边,我感到无比的痛苦和内疚,我只能通过书信去抚慰她受伤的心,她回信说”一个人要忍受的事太多了,我们都要学会忍耐”。我俩就这样怀着对彼此的思念不断通信,玉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省里唯一的化工学院,她搬到学院住宿,从此,我俩都稍稍安下心来,各自勉励,我们也谈到将来,我们都认为共产党反封建,当然也反对封建婚姻,因此,我俩都相信我的大姐会有一天觉悟过来,同意与我解除婚姻,我们大学毕业后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怀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怀着对以往甜蜜岁月的眷恋,我们在各自的大学里努力学习,过着紧张的学生生活。1953年夏秋,我忽然接到玉芳姨妈的电报,上写”芳病危,速归”。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将我击昏了,我不顾一切地向所有好朋友借钱,五十年代都是穷学生,几个同学好不容易凑够了我会去的路费,经过三天三夜长途汽车的颠簸,(当时还不通火车)终于到了省城,我直奔姨妈家,进门我就吓昏了,三天以来我不吃不睡只盼着玉芳病愈的心一下收紧了,因为我看见她姨妈哭肿的眼睛和桌上黑色镜框里玉芳的照片,我几乎瘫倒在地,姨妈将我扶坐在椅子上,告诉我:”德勤,你来晚了,玉芳已经去世…”。便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我的脑子像被响雷炸开了一样,我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相信,我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过了很久,姨妈和我都渐渐冷静下来,她才慢慢地告诉我,”玉芳参加了学院组织的下农村帮助农民秋收工作队,去了少数民族地区,那里卫生条件极差,蚊虫非常多,玉芳感染了乙型脑炎(俗称大脑炎,是一种嗜神经性虫媒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蚊虫是传播媒体介。作者注)高烧一周昏迷不醒,送回城来已来不及抢救,因是传染病故去世当天便火化了,我将她葬在百花山,你想什么时候去我陪你,…”。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知道点头,第二天清早我便马不停蹄地向百花山奔去。百花山,一片翠绿,依山傍水,玉芳的墓就在山脚下,直到这时我才相信玉芳是真的离我而去了。我不会哭,眼泪都往肚里流干了,我告诉姨妈,”我想一个人跟玉芳呆一会”。姨妈听懂了我的话,她走开了。我拿出玉芳赠我的口琴坐在她的墓前,低声地吹起苏联歌曲”小路”。那是我和玉芳爱唱的歌?#19968;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蒙的远方——.我想起第一次与玉芳在中学的林荫小路漫步,想到她每次在台上表演我为她伴奏的情景,想到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想到我们彼此,”等你一辈子”的承诺—-等等。我对着她的墓碑说话我将几年来想说的话都对她说了,就这样痴痴地对着她不停地不断地说,说累了,就吹奏一曲她生前爱唱的歌,直到天色昏暗,我仍在说过不停,这时她的姨妈走了过来将我扶起对我说:?#24503;勤,你已在这里坐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了,不吃不喝,这样下去身体要受伤,这是玉芳不愿看到的,你还年轻,还会有好的前途,走吧!我们回家。姨妈不顾我的坚持,拉着我离开了百花山,第二天我启程返校。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很紧张,我的心情也渐渐从对玉芳思念带来的忧郁,凝重,疲惫中逐渐平静下来,我思来想去,最重要的是我应该怎样面对现实,对于前途,毕业后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由不得自己,而我的重负是家里的”大姐”,我结婚八年中,家里四位老人和一切家务都是”大姐”在照料,八年来,我的祖父母和父亲相继去世,我也就是三位老人仙逝时回过三次家,当现在我毕业在即时,我将怎样面对我这有名无实的婚姻?我必须做出决定,玉芳已经永远地走了,她像山涧的一弯清泉,潺潺地流淌在我的心中。而”大姐”却像一株松柏挺拔坚实地生长在我的家中,她敦厚,朴实,无怨无悔地替我伺候四位老人,她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良家妇女,我如抛弃她,是情理难容,我不忍,也不应该离开她经过多少不眠之夜静静地思考,深思熟虑后,我决心与大姐共度一生。1954年大学毕业分配在成都的水利部门工作,一切都安定下来后,我将母亲和大姐接到四川,1956年和1958年我们有了两个儿子,母亲在1961年饥荒年代逝去,大姐因没有文化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我毫无后顾之忧的一心工作,回家便专心辅导两个儿子功课,他俩一直学习优秀均考上名牌大学,现都成家立业。我与大姐几十年的相处,我获得的是平淡,安详,和睦,这就足够了,我感谢她为我奉献了她的一生,她照顾我和儿子那种心甘情愿到不惜牺牲自己的程度,使我感动,面对这个传统而善良的大姐,我告诉自己决不能伤害她,只有她的存在我才有一个完整的家,我的大姐在77岁时因感冒转肺炎,高烧十几天后死于呼吸衰竭,她走后留给我和孩子们的是无限的怀恋!!
今年,当我81岁生日时,大二子一家四口从美国的依特律回来,小儿子一家请来了亲朋好友,兄弟二人给我这个老爸摆了一台丰盛的寿筵,在喜庆的气氛中,我拿出保存了60多年玉芳赠我的口琴吹奏起”小路”。许多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夸我老当益壮,这么大年纪还能吹的如此传情,在他们的一片赞扬声中,我似乎看见两个女人远远朝我走来,一个青春洋溢,娇小美丽,一个温,良,恭,谦。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女性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欣慰,我知足,在举杯祝酒的同时,我在心灵深处祝愿她俩安息!!
2011年10月21日 完稿
7103 个字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