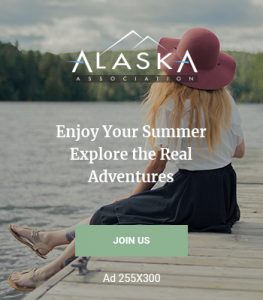略知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晓得陈布雷先生是蒋介石的高参。其实陈布雷先生是先获文名﹐而后从政。他几乎是中国第一代报人中的詨詨者﹐民国之前已名扬天下。听母亲说﹕陈布雷先生瘦高体弱﹐文质彬彬﹐不苟言笑。
我的舅舅讲﹐抗战时期在重庆﹐外祖父和陈布雷先生同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舅舅们到上清寺侍从室找外祖父﹐曾与陈布雷先生一起吃饭﹐发现陈布雷先生肠胃很坏﹐每餐饭只能吃烤焦的面包。陈先生平时讲话很少﹐却为人甚为热心﹐帮人办事极严肃认真。
外祖父讲陈布雷﹐则称布雷先生是个老失眠家﹐每夜就寝必须吃安眠药三片﹐然后也才能得到三四个小时睡眠。他的小药箱里﹐装满各式各样的安眠药﹐用外祖父的话说﹐琳琅满目。外祖父多年写作为生﹐自然也失眠﹐但经过香港逃难﹐有一阵子可以倒地便睡。到了重庆﹐进委员长侍从室﹐主持《中央日报》﹐每日写文章之后﹐旧病复发﹐又开始失眠。但他失眠﹐远没有陈布雷先生那么严重﹐桌子的抽屉里只放一种安眠药﹐需要时吃半片一片﹐就能够睡了。每次外祖父自己存的安眠药吃完了﹐就跑到陈布雷先生的小药箱里去挑选﹐领取一些﹐补充自己的抽屉。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看到抗日战争已经能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决定亲自写一本书﹐提升民族尊严意识﹐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凝聚抗战胜利意志。他同陈布雷商议﹐准备讲写作任务交给陈布雷先生完成。可陈布雷先生因为长期严重失眠﹐脑力体力均不济﹐便推荐外祖父代劳。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传﹐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见陈布雷先生那种身体情况﹐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相怜﹐拔刀相助。
不过相比于外祖父较为激进的性格﹐陈布雷先生更加谨慎稳重﹐那是确实的。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筹备时期﹐国民党吴铁城秘书长请外祖父去一趟上海﹐外祖父外婆便同行﹐在上海狄斯威路的房子里住﹐那是当时我的父母亲的家。外婆做了几个菜﹐外祖父请吴秘书长及上海各界的朋友﹐聚集家里便餐﹐商讨政治协商会议遗留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后﹐那就成了外祖父的日常工作﹐往来沪宁之间﹐与各界会商。每有什么结果﹐便通过上海市政府机要室﹐向吴秘书长报告﹐或者直接报告蒋介石。
七月初外祖父接电报﹐马上赶往庐山牯岭﹐晋见蒋介石。然后会见陈布雷先生﹐陈述他在上海同各界商讨筹备国民大会的情况。事情之多﹐两个人会面了两次﹐谈了四个多小时。结果是陈布雷先生大为惊骇﹐对外祖父说﹕原来国民政府要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是根据你的报告﹐你的责任也就太大了。从这番话可以想见﹐如果换了陈布雷先生﹐他就绝对不会像外祖父那么去做了。而且外祖父汇报过在沪宁的协商工作之后﹐接到命令﹐留在庐山上办《中央日报》庐山分版﹐不必再下山了﹐不知那与陈布雷先生对外祖父的关心有没有关系。
陈布雷先生跟外祖父同事以前很多年﹐就已经相识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外祖父根据英国法律﹐撰文抨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非法行为﹐发表在《公理报》上﹐一石击起千重浪﹐甚至招致英国领事对商务印书馆提出诉讼﹐当时外祖父在商务做编辑。因此外祖父一夜之间﹐成为上海名人。上海学术界十个人联署发表宣言﹐抗议南京路残案﹐外祖父乃其中一人。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那一宣言发出声援。这个社论﹐就是陈布雷先生的亲笔。此段历史﹐请参阅本书”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一文。
北伐战争之后﹐在上海南京两地﹐外祖父和陈布雷二人﹐同时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海复旦大学校庆﹐外祖父和陈布雷先生同时应邀出席。陈布雷先生讲话只几句﹐外祖父讲了一个多钟头﹐到吃饭还停不下来﹐此事给陈布雷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外祖父在南京中央大学做教授﹐陈布雷先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做政务次长。外祖父写文章犯忌﹐上海警察局出动搜查新生命书局﹐密报外祖父言论违纪。外祖父闻讯﹐写信给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辞职谢罪。朱校长便去找陈布雷先生和中宣部长刘卢隐先生疏通。刘先生说他不认识陶希圣﹐陈布雷先生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遇见这个人﹐他的毛病是锋芒太露。此次风波﹐最后是中组部长陈果夫先生给外祖父写信﹐教训一顿﹐算做解决。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外祖父一家都居住香港﹐仅母亲一人在昆明就读西南联大﹐两个月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万端。因为高陶事件﹐日军对外祖父恨之入骨﹐曾几次派特务到香港﹐企图谋杀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严密保护而未得手。现在日军占领香港﹐他们马上开始大规模搜捕外祖父﹐各地报纸经常发消息﹕日军在某菜园捉到陶希圣﹔日军将陶希圣剥皮抽筋﹔等等。母亲在昆明经常读到这些标题﹐不知真伪﹐惊恐万分﹐日日以泪洗面。
忽然一天﹐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把母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是重庆陈布雷先生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转给学生陶琴薰﹐通知母亲﹐外祖父已经逃离香港﹐回到国土﹐正在往重庆的路上﹐叫母亲不要太心焦了。同时母亲接到外祖父从广东韶关寄来的汇款﹐证实了他的安全。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原来在家里听外祖父讲过陈布雷那个人﹐并无印象﹐接到这封电报﹐使她感到陈布雷先生的亲切﹐她曾马上写过一封信﹐感谢陈布雷﹐并且询问外婆及弟弟们的消息﹐那信也是请蒋梦璘校长转寄重庆的。
母亲转学到重庆后﹐才知道陈布雷先生给蒋梦璘校长的那封电报﹐并非外祖父嘱托他发的﹐而是他接获外祖父安全逃到内地之后﹐了解到母亲的心情﹐自己主动发给蒋梦璘校长的﹐足见陈布雷先生感情之细腻。为此母亲在重庆期间﹐曾专门当面向陈布雷先生道过几次谢。
事实是﹐外祖父化妆从香港逃出日军魔掌﹐到达广东脱险之后﹐做的头一件事﹐是找到一家邮局﹐给重庆陈布雷先生发个电报﹐然后给西南联大的母亲汇了一笔款。此段经历﹐请参阅本书?#39321;港沦陷?#19968;文。
外祖父辗转回到重庆﹐因外婆一家还在桂林逗留﹐他独自一人便先借住重庆上清寺美专校街一号﹐那是陈布雷先生公馆的另一小院内小楼之上。从此外祖父与陈布雷先生一起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陈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顶头上司。后来外婆一家也到了重庆﹐母亲也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全家团聚。那时期内﹐母亲和舅舅们常有机会见到陈布雷先生﹐还在一起吃饭和跑空袭警报。战后父母结婚﹐也是陈布雷先生的弟弟《申报》社长陈训悆先生做母亲的介绍人。陈布雷先生去世后﹐其职便由外祖父接任。
作为朋友﹐陈布雷先生对外祖父相当地了解﹐知道他写文章用语有时比较激烈。作为上级﹐陈布雷先生也对外祖父相当地保护﹐化解他因文字而惹起的麻烦。一九四七年初﹐外祖父看到国共已无和谈可能﹐战争势在必然﹐便连续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吁请各界睁开眼睛﹐保持清醒。他甚至用了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的故事﹐预言国共难免在淮河流域再打一场新淝水之战﹐决定国家存亡。
这篇社论被当时在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邵立子和雷震先生看到﹐便找到陈布雷先生告状﹐说那都是反共言论﹐妨碍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已经引起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抗议。然后邵力子又对陈布雷说﹕雷儆寰认定﹐《中央日报》现在是CC系办的了。陈布雷先生听了大怒﹐立刻派人找来雷震﹐痛加申斥。当时雷震任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负责协商各民主党派意见﹐比较接近共产党。
斥责过邵立子和雷震之后﹐陈布雷先生也找到外祖父﹐转告了两位左翼民主人士的意见﹐外祖父坚持说﹕新淝水之战就在眼前﹐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警告国人。后来的事实﹐不幸被外祖父言中﹐不到两年﹐就发生淮海大战﹐就是当年发生淝水之战的故地。
陈布雷先生是浙江人﹐与我的父亲同乡。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陈秀(左加玉边)和陈琏﹐与我父亲在杭州师范同学。后来父亲自上海暨南大学转到重庆中央大学﹐又跟陈琏同学两年。因为夫人生育陈琏而逝﹐陈布雷先生十分悲痛﹐从此未续娶﹐并把陈琏小名叫做涟涟﹐以示如泪﹐足见其感情之深之重。
在杭州师范读书时﹐父亲是跟陈秀(左加玉边)同班﹐但他同陈秀(左加玉边)的妹妹陈琏却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后来虽然两人就读不同学校﹐却似乎仍然在心里保持着感情。据说陈琏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她的箱底一直存着父亲写给她的信。直到后来陈琏接触了袁永熙﹐而后做了恋人﹐才断绝了同父亲来往的念头。
我的母亲先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那时陈琏也在西南联大读书﹐两人同学﹐也是朋友。后来她们又先后转入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同学。也是这时﹐我的父亲也转到中央大学﹐与陈琏同班﹐但此时两个人已经是两条铁轨上跑的火车﹐永远也走不到一起了。
因为两个父亲同一办公室﹐身世相近﹐两个女儿自然也来往密切。每逢周末﹐母亲总迫不及待从沙坪坝赶到重庆﹐到上清寺委员长侍从室找外祖父﹐几次相约﹐陈琏却从不同行﹐似乎与其父陈布雷先生不大和睦。此事让母亲觉得很奇怪﹐但她当时并不知道﹐陈琏那时已由袁永熙发展为中共党员﹐所以要跟父亲陈布雷先生划清阶级界限。不过我想﹐陈布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觉出女儿的政治背叛﹐只是爱女之情笃笃﹐不肯点破而已。
抗战胜利﹐国府还都。母亲和陈琏也都跟随她们的父亲﹐回到南京工作。可母亲并不晓得﹐虽然陈琏极力躲避父亲﹐中共却要利用她这层父女关系﹐从事政治军事活动。国共战争期间﹐中共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安插了许多谍报人员﹐收集国军布防及调动情报。陈琏曾多次接受中共命令﹐动用陈布雷先生的私人座车﹐出入国府和南京各防地﹐以其父特权避免军警搜查﹐把重大军事情报送给中共方面。
后来终于事发﹐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被国民政府警察局逮捕。尽管政治立场不同﹐毕竟父女情深﹐陈布雷先生亲自出面﹐将女儿保释出狱。陈琏无法在南京继续潜伏活动﹐便秘密经上海转往苏北中共根据地。据母亲回忆﹐陈琏在上海躲避的几日﹐就住在狄斯威路母亲的家里。但是从陈琏离开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
时局骤转﹐陈布雷先生自杀身亡﹐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外祖父跟着南撤台湾﹐中共随即建政。陈琏进了北京城﹐任团中央部长﹐她的丈夫袁永熙做了清华大学党务书记﹐都是中共高官。也是这时候﹐父亲才彻底明白﹐当初在重庆中央大学﹐为什么陈琏同他坚决地断绝了往来。因为她是共产党员﹐她的上级就是她的丈夫。
一九五三年﹐父亲被中央政府从上海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外文出版社。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社里发给他一张国庆观礼票。所以十一那天﹐他到天安门观礼台﹐观赏国庆阅兵和游行。也是命运捉弄人﹐就在同一个观礼台上﹐父亲与陈琏相遇了。但那时﹐一个是中共的高官﹐一个是被使用的旧知识分子﹐地位的悬殊已如天壤之别。两个人简单地寒喧几句﹐父亲事后还感叹﹐当时就看得出来﹐陈琏是迫于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努力拉开同父亲的距离。
因为父亲母亲都同陈琏是好朋友﹐都对陈琏表示巨大的好感和同情﹐所以我很愿意相信父亲和母亲的感觉﹐愿意相信陈琏确是个好人﹐不幸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利用了的善良青年。后来母亲也随着父亲﹐从上海搬到首都﹐可作为国民党大战犯之女﹐始终不敢同陈琏联络。虽见不到﹐母亲仍是一直很关心陈琏的情况。特别是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陈琏的讲话﹐并且因此受到鼓舞﹐给周恩来先生写了一封信﹐从而获得特殊照顾﹐能够在最黑暗的年代﹐保持同台湾外祖父的通信联系。仅从此一点﹐我也必须对陈琏女士表示谢意。
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大会﹐陈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之后﹐周恩来头一个站起来鼓掌﹐于是受到中央关注﹐并在几天后全文刊在《人民日报》上。陈琏的讲话是这样的﹕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话虽然是如此说的﹐掌虽然是那样鼓的﹐现实却终究没有这般美丽。
虽然陈琏和袁永熙夫妇﹐曾为中共建政出生入死﹐甚至背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中共内部的打击和清洗。一九五七年陈琏的丈夫袁永熙被划为右派﹐撤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之职﹐铃铛入狱。陈琏因此离婚﹐我的母亲听说后﹐曾经极度难过﹐不肯相信。她知道陈琏很爱她的丈夫﹐两人从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时期开始﹐数十年生死与共﹐不可能一夜之间形同路人﹐他们的离婚﹐必是残酷政治压迫的结果。
后来陈琏调出北京﹐回到上海﹐消息越来越少。文革初期我借革命串连之便﹐回上海访故居。临行前﹐母亲还特别嘱咐我﹐设法打听一下陈琏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华东局去看过大字报﹐可惜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陈琏在上海屡遭批斗﹐不堪屈辱﹐同其父陈布雷先生一样﹐自杀绝世。那时父亲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连那消息也传不进去﹐倒免了他伤心。
母亲获知那恶耗之后﹐许多天默默无语﹐神若有失﹐不可终日。我想母亲一定是又想到她们各自的父亲﹐她们两人的同学生活﹐她们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她们共同的不幸。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