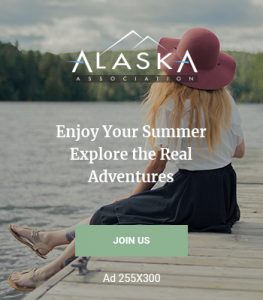怕天公不作美
也怕地不给力
最怕听到”程政委说的”
文化不是用来显摆的
搞不清谁是阶级敌人
游走于阴阳之间
迷茫于红黑和白之中
现在一讲起历史便是明清宫室秘闻,或是英雄豪杰,手刃倭寇之类,前几十年的发生的事倒让人淡淡地忘却了。历史就像个小媳妇被后人任性涂抹,连经历过的人都怀疑她存在的真实性了。当政的自己不说真话,销毁证据,还告诫卸任的一切秘密要烂在肚里,不许传出。所幸小民不属那列,还有机会为知青时代留一记录,补遗拾缺与波澜壮阔历史同行的小人物。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追求,有不同的时代的英雄枭雄或狗熊,正如现今忽然蹦出个马云,那时稀罕的是焦裕禄。兄弟不才,下乡时节当了几年生产队长,没见过现在乡镇管事干的那些拆房逼税,上环刮宫的耀武扬威,也没轮上入党提升,倒是涕泪一把,溴事一摞,小晒一笑,以正视听。
一不小心,土袍加身
按常规说,我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是不可能在乡下生产队当上队长的,但谁叫我们正好生在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年代呢。
书没读几天,全部学生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中小学都不上课,专读语录。后来发觉国家这样折腾也不是事,那管事的大手一挥,读书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全部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本人成为那上千万分之一,注销了城市户口,去了那江西井冈山专区下乡插队。
那井冈山在当时中国可是个有名的地方,虽然比不上圣地韶山,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任当局发迹的地方,红军在那里凭险阻挡国军进攻,站稳了几年脚跟。所以能到那里插队下乡也有点沾了仙气的感觉,和同窗写信聊天仿佛底气也上来了一点。我所在的队虽然是在山下,但听说那山上家家是烈属(参加红军,战死沙场),便还是心怀崇拜,有虔诚的心态。所以虽是城市学生一个,做起活来还是努力有加,不愿输给农人,几年下来各种农活包括山上的活(四面有山,先人在荒山栽种了油茶树)都学会了。但在农村,要让农人另眼相看,还必须做的强悍,精到。试举几例:
农活中首要的是力气。这力气分两种,一种是耐力,虽然不重不难,要你长时间的坚持就看你的心力是否有足够的定力。这点所有的插友农伴都能做到,虽不喜欢但无奈的力量更大,逼着您定力养成;另一种就是负重力,需要足够的体魄和意志。村里有个小伙力大嘴也大,人喊阔嘴,自持年轻气壮,整天在我们知青面前幺五幺六的。一次出工挑牛栏粪,从牛栏里挑到田里,阔嘴嘴都撇到天上去了,笑话知青没力气。虽那时人力不壮,但气还有一口,我一口应战阔嘴,称两个三百斤的担子,一人一个送到田里。结果一个装到250斤左右,阔嘴歪斜地走了几步人倒下了,没了先前的傲气,只是喘着气斜眼看着我的洋相。一看对手倒了,我又增了几分自信,结果担子再加到290斤,一口气送到田里。虽然担子压得眼睛几乎曝出,但从此后,农伴们再也不敢小巧我们,我呢,私下也有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得意。
另外,手里的活计还要做得精到,让人信服。我们插队的地方因为雨水多,历来种的是水稻,所以犁耙插秧割稻都是常规的农活。刚干起来有点难,但干久了,那儿时玩耍养成的记忆便成了技压群雄的本事。比方那犁耙田就是将土活着水,弄平整了,可以供人插秧。其实那有点像小时玩泥巴活水,活着活着感觉就来了,土旮旯就变成水镜一般的了。还有更细致的撒种谷育秧,一般都是资深老农才有这般待遇,在比水镜还水镜的秧田上洒下种谷等待秧苗出生。老农小心翼翼,侍候秧田如同对待自己的闺女,弄得好根根都像出水芙蓉。但也有失手的时候,哪天风沙太大迷失了手里的分寸,待到秧苗出生便是稀毛癞痢一般,弄得拔秧的妇女叫苦不迭。不过在我们看来也就是小时在公园的湖面上撒沙子一样,沙溅水花,一路压过去就是。于是说尽了好话,让老土地让我这样的新手干一回。因为有儿时调皮玩耍的经历,所以撒起谷来,也潇洒大气,有模有样,老土地称赞有加。从此,有老农撑腰,这最精细的活里也有了青壮年的身影。
不过,插秧是我的短板,这也和幼时的经历有关。父母为人师表,总是教育我们不要玩杂耍,荒废学业,所以插兄们玩牌发牌溜得像刘谦,弯腰插秧像鸡啄米一样,不会发牌的我只好在并排插秧时被人拉下或者关在当中,汗流夹泥,举目无亲。好在农民老表以下力多少看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没受歧视。当时腰酸无比,特别是左面,总要撑着膝盖才能坚持。看着插妹们嘻哈一阵风样掠过,常自责很久,缺乏锻炼哪。后来到了美国体检,医生大惊失色,说他从医多年还从未见过人腰椎右面有强壮的肌肉,而左边一点肌肉没有,问为什么。怪不得我左腰老酸,插秧老追不上他人呢。为什么,能向老美说得清吗,说挑了十年担子,肌肉长到一边去了。恐怕他们连担子都没见过呢。
农民虽然有时小气,但助人讲义气的古风还是深存心底的。这又要说到前面的阔嘴兄弟了。这兄弟显摆力气不假,但手活不精也常被农伴笑话。而且这兄弟脚下走路不稳,大概是外八字脚吧,凭白无故地走路会自己绊倒自己,脚花太乱。那年到山上扛木头,一伙青壮年都结伴成行,唯独阔嘴兄没人与他为伴。因为扛树除了是个力气活,还是个细心活,常常是两人扛一根木头,前面的人扛大头,后面的人要靠近树中间一些扛,减轻前面人的重量。在弯曲的山路上行走,后面的人责任更大,除了要看清前面的路外,还要预算肩扛的树尾是否会挂到岩壁,否则连人带树狼狈为奸都到沟底去了,危险大去了。这脚花乱的没人喜欢为伴。
我是新手,也没人为伴,便最后与阔嘴自然搭配为伴。这阔嘴也真的名不虚传,认真倒是认真,背上的汗我在后面都看得见,但脚法就不敢恭维了。岂止是不敢恭维,看到阔嘴脚下在跳舞简直是胆战心惊了。沪语常说脚骨弹琵琶,大概就是这般境界。要知道,那时我们肩上扛着同一根木头,任何闪失都会导致两人与生死俱进。
但怕什么就来什么。在过一条山沟时,阔嘴那脚不是仅仅在弹琵琶了,而是乱弹古筝了。山里都没路,拿着砍刀干掉荆棘能过就是路了,遇上山涧放倒几棵小树并排一下还颤颤悠悠着就是桥了。过这桥也要有技巧,要脚板打横同时踩到两棵树上上才敢用力。阔嘴就有这个胆量,那外八字还未打横就敢用力,一脚踩上去整个人连同肩上的木头就滑落在两根树当中,整个桥上就剩下阔嘴的头和肩扛的木头了。
看官可曾忘记,这扛木的另一头是还没有过桥的我。如果我经受不住那强大的震动,丢了木头,自己得个平安,虽然无可指责,但阔嘴兄弟的生涯可能由于木头的再次弹起而结束。我死顶着没让树脱肩,让闻声赶来的伙伴救起了阔嘴。那拖起的阔嘴嘴吓得更宽了,半天没合拢来。
就这样以后选举队长时,乡亲们选了我,除了力气和技术外,其中一人就提起了这话题,说是有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担当。
不过,被选为队长也属偶然。历来中国的官不是想当就能当得,每个时代都要走自己的程序。比方古代人纵有满腹经纶,也要进行科举选拔,从秀才做起。但当时不知道哪阵风吹来,说村里百姓可以自家选举队长,用现在的话就是民选了。有老爷子当官的背景,便可以入党入团,还可以坐大队书记的位子,我等没背景,又不是党员团员,纵然心中有万般念想,也是断不敢有此奢望的。但这个20多户,100多口人家的小村偏偏异类,虽然同姓吴,但事多,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结果选举会上,让我这样知青得票最多,当上了队长。
好好的城市学生不去读书,到乡下当上个队长也不是凭知识,在现在看来都是最不可思议的。但这一切都这样发生了。身在其中的时候更是只有受宠若惊,而没有今天的疑惑了。(待续)
作者简介
商慧明,现居亚利桑那图桑市,出生在上海,1968–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