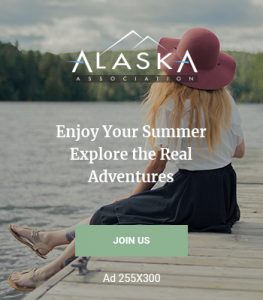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接上期)
先当弼牛温
现如今京官上任都要有地方从政的经历。兄弟虽然与他们不是一类,但升官的路径却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我的地方经历是先当牛倌,和那孙猴子混个弼马温那般。原先,农人的牛是不要人专管的。但一到农闲时分,满田的禾苗都长了起来,这牛见到绿草之类的东西就像着魔似的,见人一不注意,便狠扫一口路边的禾苗。这散漫自由惯了的牛便要人看管了。所以,早上农户们将自己的牛往指定的地方一扔,这牛就算交代给你了。本来像我这样的小伙是轮不到放牛的,但刚下乡时水土不服,脚上烂得不堪入目,弼牛温这个美差就归我了。
像当年弼马兄那样,多亏还当了一回这不入流的官,长见识哪。
(见识牛式云雨)
人说起放牛便想起”青山绿滩水草美,老牛卧倚半酣睡。肚儿圆,犄角垂,夕阳西下不思归”的境界,其实那并非是当时全部的写照。那只是经过过滤后沉淀下来的美好希冀而已。诗情画意都是闲着的人体会出来的,或者是爱虚荣的主(比如我),过去了便牛皮尽捡好的吹了。别说是酒足饭饱了,就是没吃饱的瘦牛,一见天将黑便都急吼吼地往自己的圈里奔,哪来的不思归呀。再则呢,你老是跟在牛屁股后面转悠,弄不好便踩一脚新鲜牛粪,还有什么水草美呢。
而且,这牛从来是欺生的。见你生得嫩相或看着不顺眼,这牛便劣根毕露,不是偷着掖着尝一口新鲜禾苗外,就是聚众谋反,另立山头,让你个牛郎顾此失彼。好在本弼牛温尽管新官上任,却深知其中奥妙。这牛毕竟是咱国产土牛,像咱人一样,老被人管着呢觉得不自在,便想自由自由。但没人管了,又觉得失落得很,脱离主流社会了,便放任起来了。
但,倌毕竟也是官,见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深知在专制环境下生活过的牛其实是最容易在新权威的淫威下俯首帖耳的。所以,要真正地让这些畜生们”俯首甘为孺子牛”,本官还得亮些真家伙出来。
当年弼马温建立威信靠的是那根棒子,咱没那玩意,只能就地取材了。一位插兄建议买个哨子,让牛们随哨而动。想法不错,没准哨声一响,牛们便立马急急把家还了。后来想想还是作罢,这山里满地的鹩哥(黑色,像八哥,嘴巴嫩黄),学其他鸟叫惟妙惟肖,哪天让那厮学会了哨声,还不乱套。
咱还是搞点有中国特色的,顺手捡起路边的石子教训违规的主。这一开始的技艺实在不怎么的,充其量只是”打哪指哪”的水准。哪个畜生钻到田里去了,拿起石头便砸将过去,也不管是砸到牛的屁股,还是在水田里溅起一片水花,然后远远地一迭声地吆喝和挥手。幸好那偷吃的主心虚得很,一见这番动静掉头便往山坡上跑,大事就化小了。
但,累人哪。你想,几十号牛呢!这畜生还会看样,你可以偷吃,我为什么不能尝新呢?这最初还真弄得本官顾此失彼,狼狈不堪呢。但后来本官总结了经验:对违规的要狠,不能因为你天天背犁驾辕了或有过一点业绩成果了,用人的话就是有点政绩了,上岸了就可以不追究责任了?不,本官常常将鞭子藏在背后,踱方步式地靠近那个肇事的主,乘其不备,一阵狠抽,打得那畜生夹着尾巴四处逃窜。这倒不是本官恨动物,实在是职责所在,杀鸡给猴看呢。否则。这山坡水田狼烟四起反而没和谐了。
这二来呢,出手要准。你想,老是在牛边上打个水花什么的,不能给这些违规的主有没齿之痛的警戒。这就进入了提高惩罚水准的技术层面专题了,也就是”指哪打哪”了。
这牛除了怕鞭子以外,就怕脑袋和角的震动了。动物和人一样,最有用,最能取媚于人和同类的就是脑袋了,君不见两性相爱或者长者抚爱幼者,都先触摸脑袋。但鸡飞狗跳以及牛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既爱他人抚摸自己脑袋,也怕别人和同类伤害自己的脑袋。所以石子击中牛的角和脑门星的部位是最能敲山震虎了。
不必说那技艺花去我多少时间和丢去多少石子了,反正后来只要出手准能听见那石子在两角和脑门间脆生生的响声。顺便说一句,这技艺也给以后带来了近于美好的回忆:后来进大学,一举夺得全校手榴弹比赛冠军;再以来在学校任教用粉笔头击中作弊学生的眉心,悄然保留了学生的自尊。不过,这是后话,后话,和弼牛温小有关系而已。
果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牛们开始知道了自己的劣根性,都能安静地吃草了,尽管还时不时地偷看一下那高竖的寨旗(为了让牛们懂得尊重权威,我特砍了根长竹,竹梢上系了个红布条,以为本官图腾)和边上貌似懒散的我。我暗自窃笑,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哪。
和牛们相处多了,还长其他见识呢。不怕见笑,那时的年轻人对两性之类的事知之甚少,不像现今的孩子动不动就来个生离死别,以身相许什么的。不过有幸的是,兄弟放牛期间还是偷眼瞧了些许牛们苟且之事,粗通了这牛人如一的知识。
这牛人都一样,吃饱喝足了,便浪漫情结顿生。那女的挤眉弄眼地,往男牛堆里蹭;小公牛老公牛们怎经得起这番春末夏初温暖阳光的荡漾呢,便一个个雄性大发,磨角刨蹄,恨不得一下把情敌赶走,独占了那份浪漫。于是一场角与角的较量在山坡展开,这世间情色也真有这般大的力量,弄得平静的山坳里一片厮杀声。
身为弼牛温理应当一回调停官,但两军相战你调得了吗?何况这还是情战,涉及爱情。咱没法出国看斗牛,这不免费送票了么?所以,咱只管躺在寨旗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戏偷着乐。
尽管两方都亮出了绝杀手段,但总有那一方抵抗不住,落败而去。那胜出的虽然豪气万丈,却也不像西班牙蛮牛毫无理性,赢了还犟着死追活赶。国牛则不同,将对手驱逐出浪漫领地,胜者立即打道回府——不然,后方空虚,那浪漫倒让他牛占了,可不气杀老夫!于是,再一次扭捏,再一轮追求,一番惊天动地的牛式云雨尽收本官眼底。咳,咳,不说也罢。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被阉过的伙计(农村的耕牛大部分是阉过的,说是这样无非分之想)也在那里喷气刨蹄,激动得狠。这倒有点像那个太监什么的,没有能力倒有热情。好在这些主只是在边上渲染气氛而已,没有什么破坏现有格局的出格行为,本官予以了进一步的容忍。
有这点知识和没有这点知识可是大不相同的。那天集牛进山,那牛刚一出村就见到它心仪已久的对象了,便轰轰烈烈地爬将上去。咱看惯了,任其浪漫。可同行的还有一位插妹,哪见过这种架势和世面,便哭着喊着叫大伯叔叔,快去救救小牛吧,那牛快要被压死了耶!那小母牛虽然个子小点,但也在享受浪漫呢。所以农民大伯叔叔阿姨们一个个讪讪笑着,不搭理这位插妹。
怪不得这位插妹的,谁叫她没做过弼牛温呢?
(粗通牛语)
大凡文章写到鸟语的境界了,最不济的也应该是一片人和自然生物的和谐景象,比较级的呢则是浪漫幸福的前奏,最高级自然是仙境了,婉转多情,飞天环绕。但涉及牛语了会不会也有这般美妙环境的描写呢?待我细细道来。
牛发声称”牛语”实在是太书卷气了,牛叫就是牛叫了,最多是个哞什么的,实在雅不到”语”的!那语都是指百灵、云雀之类的鸟们在花丛树阴处的宛转低吟,那漫天高亢的杜鹃都进不了此列呢,你一个老牛还充什么斯文呢?但这牛叫外行是听热闹,听多了便成了内行,本官大言不惭,就是听出点门道来的那种。
先说这黄牛。这南方的黄牛如同中国南方的人一样,小种小样,别说没有北美野牛那般楞头野气了,就是和国内北方的秦川牛们相比,也差了一个级别。这南方山水相隔太多,人交通不便,还来个近亲结婚呢,牛更是如此了,久而久之,这种气便往小里延伸了。
但那牛叫并没有因为个头小而逊色于秦川牛什么的。相信看官一定有相人的经验,别看某位伟岸英俊,可说起话来,却怯生生地露着奶气,一股娘娘腔;而那位貌不惊人,身高不足1米60,说起话来却声若宏钟,气震山河。咱那地方黄牛就是这个德性,叫起来用”哞”来形容都太委屈它了,说它叫起来像”吼”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咱那地还见华南虎,叼鸡啃猪的事常有所闻,但很少听见有啃牛的,想来就是这牛哞太牛了,吓得那虎也不敢下嘴了。
不过细听起来,这牛哞还是有三六九等,有个男女之别的。这公牛呢底气足,那肩上的肉疙瘩也大,常常是前腿站在高坎,一耸肩便吼,声音洪亮悠长,倒也有点气吞山河的味道。你若是从未听到过黄牛叫,准保会有猛一惊的感觉,说它有狮吼之威也不为过。那叫声并不常见,不是太晚了通知主人想回圈,就是闻到了相好的气味,以显示男牛的气概呢。
若是那初长成的小蛮牛,见到同类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和帅相,叫得次数就多点。但腔调不如老牌公牛,一听便知道是学它牛的旧歌老调,吓唬人,也乘机抬高一下自己。
那母牛呢,虽然也是一般地吼,但明显地要单薄一点,而且也短促得多。其实她有时是不用吼的,吸引男牛本各有高招,哞一下是自我吟唱,增加自己的品位呢。不过惹事生非,往往”媚”一声就能挑动情色大战倒是不少见。
说牛叫也不要漏了那阉牛。其实农村里最多的就是它们,农民最喜欢的也是它们。它们可以说是任劳任怨,身体看上去强健,只管低头干活,即使吃饱喝足也不会参与春风荡漾,最多也就是跟着它牛哼几下。但那叫声实在不敢恭维,像那被阻塞住的唢呐和小号,好不容易憋出一声来,又由于底气不足而收音了。
哦,还有水牛叫呢。那水牛可是南方的特色,个高力大,皮厚毛稀,除了怕热喜欢到水里打个滚什么的,作为畜力几乎是没有什么缺点的。但这硕大的个子叫起来让人简直不认为是牛在叫唤。与黄牛比较,那叫声只能叫”呃”,好像是从漏风的风箱里有幸挤出来的哼哼。倘若是母水牛,那哼哼还有点像单簧管独奏,呃的清脆圆润,收音结尾略带降调,像语音中的入声。但公牛就不是这般了,虽然还是通过鼻孔发出的声音,但那声音高亢得多,悠远得多,有点像萨克斯管的声音。美中不足的是,这公牛在叫时总希冀马上得到回音,若不能马上得到回音,那最后的拖音中就带着明显的哭腔,如:
”呃————哇—-”
但若见到了呼喊的对象,主人或母牛,那最后的拖音自然就充满了欢快。
这听多了便自然会模仿。但要达到惟妙惟肖更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奏效的,常常是感到有抒发牛歌的愿望了,还必须前后左右看一下有没有插兄或农友们,特别是那些爱嚼舌的大妈大婶姑娘们,确定没人,便在山林里扯开嗓子练一遭。
这天下的事从来没有办不到的,只要喜欢或无奈。兄弟当时还真具备这两方面条件,所以哼着喊着便进入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常常是太阳落山,集牛回家,一点少了哪只公牛,便小母牛的干活扭捏哼哼唧唧一番;少了女同胞,则惊天动地一声男性长哞。保准,那掉队的主会从树林里探出头来,屁颠屁颠地追赶上来。倒也省事,一张嘴就来。只是可惜了俺那石子功因此荒废了许多。
悄悄地自吹一下,识别牛叫也非一日之功。如果当初你也能在那在山林河滩间此起彼伏的牛吼中判断出各牛的性别和相貌,那本弼牛温就也会面临竞争上岗的境遇了。
这牛语功初露江湖是在一次修补赣江防洪堤的工程之中。当时插队在赣江附近,一到农闲时分便兴修水利,以保来年安顺,这是农村的常规之事。这赣江堤的修补每年都要集中大量的民力,常常是几千人集于一段堤坝干活,热闹非凡。为了方便,农民常将自己的牛散放在河滩上,这一放故事就出来了。
那天两头水牛打起来了。当地有这样的话流传”不怕婆娘(老婆)吵架,就怕水牛打架”说的就是水牛认死理。这黄牛打架,拿个鞭子一扬,两个冤家马上分头逃窜。用这招对付水牛可不行,弄不好这牛会顶你,顶怕了你,回身再和那牛斗。
顺便说一句,这牛从来不是宽宏大量的。什么任劳任怨,都是文人在边上瞎感慨。牛实际上是很记仇的,你这次打了它,它每次见到你都会斜眼瞧你,且不说牛之间的争风吃醋了。料定这次这两位也是宿敌,所以一交手,只听得水牛角交错作响,煞是激烈。
乐坏了的是堤坝上几百上千号民工,整天挑担运土枯燥无味,偶一见这等乐事,便齐刷刷地丢了担子,在大堤上摇旗呐喊来了,公社主任县长来了也不怕。愁的是那两个牛主人,拿着小鞭在边上干着急。
我对周围光着膀子的农友说,我准保让这两头牛歇手。农友们哈哈大笑,你一个小四眼能—-?
恩,我点头。不信,我们打赌。
这眼见着彼乐子未落,此乐子又起,农友们又起哄了,以一瓶土烧(高粱酒,8角一斤)为赌注辍合赌事。于是,本牛倌平生第一次受到这般前呼后拥的待遇,由大堤来到河滩两牛交战地。
我吩咐那牛主人做好准备,只要两牛一发楞,各自便偷空拽着牛缰绳就走。然后乘人不备,俺按着半边鼻子,哼唧出那小母牛平时的扭捏腔。让周围农友折服的是,此腔一出,那撕杀中的俩牛不约而同抬起头来,四周张望。这牛主人也配合得是好,一猫腰捡起缰绳,拖牛就走。一瓶土烧就这样到手了。
晚上与那赌友共饮土烧,那输酒的主内心不服,还追问,你怎么哼一下,牛就不干了呢?咳,你想哪,两个汉子为一个女子争风吃醋打得头破血流,那小女子发急哭叫,你们再这样我就跳楼——哪有不歇手的理!咱哼的是牛调,传达的是这人理,能不成功么?这输酒的也枉作了这些年田了,老大不小了,连个公母牛的声都分不出,还问这等初级问题!
(牛如其人)
我们从小受了很多关于牛忍辱负重,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教育。但,牛在生活中似乎不是那么永远任劳任怨,规规矩矩的。那些年被丢到乡下去,天天与牛打交道,便有了一点另外的体会。
牛是有其公认的脾性的,但由于接触的环境和调教人的不同,其个性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笔者下乡的井冈山地区,由于地处丘陵,田地起伏不平,耕作主要靠牛耕。那时牛属于生产队集体财产,分散到各农户代为饲养和耕作,生产队每年提供给饲养户一定的补偿。这样,人牛朝夕相处,知己知彼,牛自然就开始性如其人了。
我第一次用的是叫”云根崽”的牛(补充一句,牛都没名,谁养就叫谁的名)。那牛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主,走路特快,一背上辕便瞎走,犁田没个正路。那天我累的够呛,让邻田的农人笑了个半死。后来才知道,这牛性取决于初次训练的人,若训练者农活不精,耕田左一下又一下的,以后从此这牛就二把刀,干什么都会,干什么都不行。
这就说到牛主人了。这位在咱那队好歹是个干部,大队的贫协委员(贫下中农)和治保委员(治安保卫),但农活么,老农们一提起他便撇嘴。原来此兄为三兄弟之一,土改那年,他生性好赌,将父亲给他的家产全部输尽,划了个贫农成分,他的俩兄弟则辛勤耕作,保有田产,分别划为地主和富农。尽管农活不精,但这并不妨碍贫农出身的他开会时骂骂他的地富兄弟,时不时地再挂个贫协主席的头衔到处忆苦思甜和开会。不知道他有什么苦可忆,反正他去开会忆苦,我们知青就痛苦了,因为他出去开会时我们总要用他那二把刀牛左一斜,右一歪的犁田。
还有一次用的牛更奇怪,每犁一个来回的地,这牛哥就是站在田垄上不肯转身再次下田,任凭你吆喝或用鞭子吓唬都没有用。我寻思牛蹄子里是不是嵌入了刺,便帮这哥们洗脚找刺。弄得我一身泥水,这畜生怪癖依然如故。后来又是农伴说出了其中的原由。原来那牛主人是个视烟如命的瘾君子,每犁一来回地都要掏出烟斗来上一罐,久而久之牛便养成了习惯,爬上田垄,借光享受一下主人吞云吐雾的短暂安逸。我们呢,用其牛就暂且人如其牛,与牛同进退辛劳和歇息了。
晌午歇工人回去吃饭,牛则放在四周山坡上,下午开工再将牛牵回。长久在缰绳和犁辕的控制下,难得享受一下自由,最可见各路人牛英雄本色了。那本分点的老农,临别拍拍牛的额头,那意思是别走远了,误了下午的工。吃饭回来果真见那老牛在那树阴下等着呢。奸猾点的呢,扬起鞭子狠狠甩下,唬得那牛一个机灵窜出老远。那牛煞是聪明,明白主人的意思,赶紧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猫着去了。那主人吃完饭便钻山越岭找起牛来了,一找一个下午,待大家收工了,这主牵着牛从那山林深处慢悠悠地晃出来了。那时在生产队干多干少一个样,那牛和人一样便享受中国式的大锅饭幸福了。
奸猾偷懒的人也会受到牛的捉弄。那天那位又去找牛了,当然也可能躲在树下阴凉处打盹去了。等了许久,也不见主人来领,那牛倒急了,心想,做什么也不要太过分,好歹也要划拉几下田吧,就径直地从躲藏的树丛里钻出来,老实地站在犁前等待主人的到来。可主人仍在春宵苦短的梦中呢,所以有正义感的老农们和喜欢嚼舌的、妒忌的的农友们以及气愤的管事队长纷纷感慨,人像牛那样有点良心就好了耶。
不过,牛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主要的畜力,所以尽管有人喜欢拨个小算盘,弄个小插曲什么的,大多数农民还是爱牛如命的。春耕夏种时满田满地都是吆喝声,原因就是农人的鞭子总是高高扬起,轻轻放下,很少有人会真的抽在牛的身上,吆喝只是一种吓唬牛的样子而已。除非,那天小干部大干部都来视察了,本座牛懒散惯了,在领导面前也一个懒样,牛主脸上挂不住了,下鞭就重了。
不过领导们一走,人牛如一,说不清是牛像人还是人像牛,大家犁田的脚步都放慢了。
这牛之初或许和人一样,也是性本善的,恶人教之,善人训之,牛便各得其果了。
(也有生离死别事)
这牛和人相濡以沫,久而久之便会相互产生默契和感情了。所以本牛倌尽管也惩治犯规调皮的牛,但还是看不得宰牛的场面。中国的农家牛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要落个被割头剥皮吃肉的下场。牛大概也知道这种结局,尽管也驯服地听从主人,但和人的关系却没有像狗和人类的关系那样亲密无间。
所以,每当老牛面临宰杀的前两天,牛都特别的警觉。那平常温顺的大眼睛出现的恐惧的眼神,眼球突出着,连那平时低垂的长睫毛都向前挺着,人一过来就拿角对着,不让人靠近。
村里一婆娘十余年养一牛,牛老无用被绑待宰。但任何人靠近它,牛总是发出低沉的吼叫,吓得刽子手们不敢动刀。无奈,主宰者只好请婆娘来安抚。那婆娘本身就因为老牛要宰,动了感情,弄得眼睛红红的。眼见得这朝夕相处的伙伴被绑在沙场,婆娘眼泪更是像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婆娘一来,牛果真不吼了。只是看见牛也流泪了,那豆大的泪珠”啪嗒啪嗒”掉在地上很快将地面打湿了——
一般乡间宰牛的程序是这样的:主人牵着牛走到预定的绳索活套中,抽紧放倒,然后强力扳歪牛头,下面便血腥场面了。那天杀的是头老水牛,路都走不动了,所以屠夫们松懈了一把,被牛挣脱了。
前面说过,牛从来是记仇的,何况这是生死之恨。那牛一起来,就立马成了不愿意做奴隶的牛英雄,没有一点老牛步履蹒跚的模样,怨有头债有主地认准了绊倒它的那位,狠命地追去。
脱缰的马是狂奔,逃离绳索的牛也一样。屠夫们见多识广,见牛绳索一断,就知道大事不好,立马作鸟兽散,四下逃跑,全没一点雷锋的舍身精神。悄悄地说一句,本牛倌虽然和那牛熟络,但红了眼的牛是不会念旧情的,所以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逃跑大军。
我想那牛同绝望的人一样,想反正是个死了,找个垫背的吧。可怜的是那个被追的壮小伙,平时持着一身肌肉喜欢在知青面前吆五吆六的,队长见了他也让他三分,现在跑得比狗还快,边跑还恐惧地大喊。看官想必没见过这等场面,但可以想像一下,后面是一头疯了的老牛舍命狂追,前面是一个几乎被吓疯了小伙夺路而逃。
眼看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眼看牛的悲剧就要变成人间的惨案了,小伙子灵机一动,从村口那V字型的树(树根基长出两个巨大的分支)穿过去了。都说牛认死理现在又是一证,那牛不从边上绕过,偏偏也要演一下穿越,结果因为肚子太大,被卡在两树之间了!那四条腿纵是再折腾,也无力回天了。
顷刻之间,悲剧又是牛的了。
本倌不是假慈悲,内心真的很复杂,很纠结。天天和这些牛友相处,不说友情,总有点熟念吧。但世间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动什么都可以就是在这里别动感情,你挺身而出,捍卫牛的权利了,那些端着饭碗半年一年没肉吃的农民兄弟大伯大叔大妈大嫂们倒和你反目了。
而且,喜剧和悲剧之间转化是很快的。昨天还在田里共建新农村的和谐呢,今天立马成为食肉集团和肉的关系;刚才几乎是牛魔王的天下了,一个突发事件又让老牛回归为盘中餐了。
所以牛倌也感叹,世事难料呵。
(待续)
作者简介
商慧明,现居亚利桑那图桑市,出生在上海,1968–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