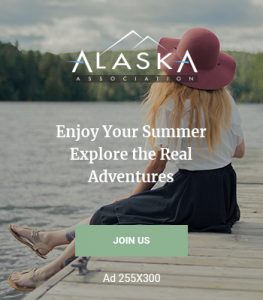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编者按)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我们在这里,美国亚利桑那州,有的人留下来了,有的人海归了,在时间和空间的交界点中,有很多分秒组成的故事,在太阳鸟亚省华人网中,我们看到张肇鸿,气如虹,文若,慧明,凤鸣,心水等很多老侨用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首先感谢他们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移民的成长足迹。”太阳鸟”专栏作家汪静玉,根据生活在凤凰城女人的真实故事,撰写出了小说《凤囚凰》。
凤 囚 凰
汪静玉
5
后来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很傻的办法,这个方法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摧残,但也就是这个办法,让我终于成功地从严格力身边逃脱出来了。
有一天,他带我去他朋友蚊子家吃饭。我们三个人喝酒,其实也就是他俩喝酒,我只是坐在那里陪他们聊天。正喝着酒,严格力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个尖锐的嗓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因为惊吓,对方的声音抖得很厉害,而且明显带着哭腔,她说一个可能是黑社会的客人喝多了看上了她,非要带她去开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声音咋咋呼呼的,在这个异常安静的小屋里我们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和蚊子同时把目光投向严格力。
果然,严格力一听,脸色顷刻一变,急眼了,他把桌前的碗往里一推,起身就要去救她。那一刻我想机会终于来了,我拿起桌子上的白酒,咕噜咕噜直往肚子里倒,蚊子一看吓傻了,他说,你干嘛呢?然后伸手过来夺酒瓶,我一把甩开他,说,别拦我。他们看到我悲痛欲绝的样子,有点措手不及,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而我需要用这瓶白酒给自己壮胆,我咕嘟咕嘟将这瓶白酒全喝进了肚子。一瓶白酒下肚后,我开始浑身发抖,抖得不行,我快站立不稳了。在摔倒之前,我说我要上洗手间,但我却直接进了厨房。那一刻我头脑里只要一个念头:我今天就豁出去了,成败在此一举。
严格力很决绝地看了我一眼,最后还是决定英雄救美。
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我的心突然像被人挖去了一块,兀自在那里生生地疼,我在找刀的时候眼泪模糊了双眼。这时我才发现我还爱着他,不然为什么我还有痛,还有酸,还会哭,还会很伤心,那就肯定还有爱。因为什么呀,因为是初恋,因为当初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和付出。在我看来,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婚姻更是,如果有第三者夹在中间,那就什么都变味了。他使用暴力,而且想用暴力让第三者在我们之间变得合法化,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拿起刀,但不知道如何下手。我想,杀自己两刀,但万一杀的不是地方,那我不就白白送命了,我还真的不想死。我当时想,我怎么那么窝囊,不够强势,但现在想想,如果当初不是那么窝囊,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拿着刀在自己身上比划着,小伤不行,只会招来他得意的嘲笑和更放肆的轻蔑。怎么办?我脑海里突然掠过《上海滩》里许文强面对强敌从容断指的一幕,他成功地吓退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酒精的作祟下,一股热血直冲我脑门,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一刀剁在小指头最上面的一个关节上,第一刀没有剁准,第二刀啪地一刀下去,血花乱溅,小指头飞了出去,弹在玻璃上又弹了回来。我看着离我两米远的我的小指头,吓傻了。我站在这,我的指头却在那。我看着嗤嗤直往外喷的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蚊子发现我在厨房呆了很久还没出来,他开始敲门,敲了一会他就紧张起来了,他喘着气大声地说,你开门,赶紧开门,你再不开门我就用脚跺了。我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后来还是把门打开了,他看我举着手,浑身是血,尖叫道,你怎么啦?你把自己怎么啦?他很快发现我的小指头不见了,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赶紧蹲下身子,趴在地上到处找,终于在水槽边上发现了一个血糊糊的小东西。他吓坏了,慌慌张张地拿着我的小指头抱着我就往楼下跑。因为住在五楼,我倔在那里,抓着栏杆不想下楼。还顺势从他手上把手指头抢过来,啪地一下扔到楼梯口。我不想接手指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让严格力知道,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蚊子嚎啕大哭,他大概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他拿着手电筒哭着到处找,像在寻找刚刚丢失的宝物。找到后,他把我受伤的手高高地举起来,然后把我背下楼。他拦了一辆的士,把我抱了进去。他看我仍然血流不止,赶紧脱了衬衣撕扯出长长的一个布条来绑在我的手腕上,直到缠得手臂发白,又将我的手高高地举起,这才将血止住了。他摇晃着我说,你这是何苦啊,值得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吗?
我坐在那里只顾流眼泪。
蚊子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那医院的人说,对不起,我们医院不做接指手术。医生一口回绝了。那时候已经是深夜凌晨一点多钟。蚊子看看我,二话没说,赶紧又拦了一辆的士。血又开始流起来,他紧紧地捏着我的那个指头,一边高举着我的手臂,一边不停地哭,他哭得比我还要伤心。他把我送到另一家医院,这是唯一一家接手指的医院。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医生走过来,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指头上的神经和血管,说,我们不能给你百分之百把握,这个指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存活率。然后他边走边挥手,说,赶紧办理住院手续吧,马上手术。
蚊子如释重荷,他跑到前台,突然变得一筹莫展,在那里急得直跺脚,原来医院需要先交三千块钱的住院押金,否则不手术。这一下我们都急了,我父母远在偏远的山村,而他当时也身无分文。他边哭边发疯般地到处打电话,有些人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听,最后没办法,他只好给我”准婆婆”打电话,这一会他的声音都变了,他颤抖的声音说,你们如果不赶紧拿钱到医院来,手术做不成,她肯定会有生命危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没多大一会,他们就赶过来了。迅速把钱一交,医生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
那一会,我才真正开始感觉到痛了,钻心的痛,痛得死去活来。医生过来了,他闻到我一身浓重的酒味,说,你喝酒了?你怎么那么傻呀?是不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我哇地一下哭了出来。医生又摇摇头,说,你太傻了,多大的一个小姑娘。他叹息着摇了摇头,然后给我打了一针麻药。过了一会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做完手术后没多久,我就醒过来了。护士把我推进了病房,我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感觉像一场噩梦。第二天,严格力带那个女的过来看我,我估计他又喝酒了,他在病房里醉醺醺地捶胸顿足,然后眼睛红红地怒视着我,说,咋回事啊,你怎么会在这里?那个女孩子拧着一袋子水果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看了她一眼,无力地说,你们走吧,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们。她仍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看了看旁边的护士,对护士说,请你把他们俩请出去。看着那一对相拥着离开的背影,那一刻,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从那以后,他妈妈天天给我送饭,喂东西给我吃。医生说我半个月不能下床,不能动,他妈妈帮我端屎端尿。严格力偶尔也和那个女的过来看看,没喝酒时,他就不说话;喝了酒时,就在那反复问我”为什么”。有一次,他突然暴跳如雷,对我怒吼道,你为什么这样,啊,在我脸上抹黑,让大伙都笑话我,你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然后伸出拳头来捶打我。我动弹不得,同室的病友赶紧说,你要干什么呀?她都不能动了。他这才收下拳头,骂骂咧咧地离开病房。
我躺在床上,日夜寻思着如何彻底地离开这个地方,彻底地离开这个人。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姐姐华子从广州给我打来电话,她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躺在医院。华子着急了,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好说我切红萝卜时把手指头切掉了。她惊诧地说,怎么这么严重,切个萝卜会把指头切掉。我说,刚磨的刀,不小心滑到小指头上了。她要过来看我,被我坚决回绝掉了。我说医院都给我接上了,我都快要出院了。
出院前,医生建议我还要休养至少一个月,有个钢筋扎在里头,他说我的指头能不能存活,只有拔了钢筋才知道。他还交代要我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淤血和发青。就在这时,我这才真正感觉到害怕,我才感觉到我做了一件幼稚可笑的事。我站到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我该到哪里去呢?哪里是我伤口愈合的最佳之地呢?就这样我绑着砂带直接回老家了,回到了父母身边。
恢复的那段时间面临一种更锥心的煎熬,我每天看着自己的手指头,我在想,剁得多痛啊,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没有手指头多难看啊,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每天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就开始祈祷,让我恢复得跟当初一模一样吧,我需要我的小指头。母亲看我整天伤心欲绝的样子,心疼地说,我的傻孩子,切红萝卜能把指头切成这样吗?以后别再干傻事了,多疼啊。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