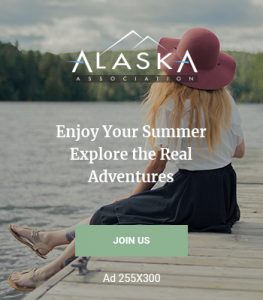凤凰城 张肇鸿
记得六、七岁时,我随父母从大城市搬迁到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城镇生活。那里环境清静、民风淳朴。由于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收入高,人缘也好。常有樵夫和渔家把鲜果与活鱼送卖到家门前,让我们精挑细选,价钱也便宜。有时母亲不想要又不好推托,只好说还未发工资,但他们说不介意,下次一起算。
河畔有茶楼,假日,父母常带我们去饮茶。我记得最爱吃的是叉烧包和萨骑马,尤其是萨骑马,香甜爽脆,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那时我脸上肥嘟嘟的,母亲就给我起了个别名叫「云吞」。大家都说我有个幸福的童年。
到一九五八年,因有海外关係,属医务高干的父亲下放到干部农场去「改造」,很久才能回家一次,人也变得又黑又瘦。母亲也因而病倒,家境自此一落千丈,十七虚龄的大姐也只有辍学到医院做勤杂,以帮助家计。
那时,大陆已进入大饥荒年代,人间悲剧一幕幕地发生,在医院里,常有「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的惨状,那是指男人因水肿大了肚子,女人因严重贫瘦,子宫也下垂了出来。那期间,每人每月配油四两,是糠油:偶尔有肉配给,但要絶早去排队,迟到就没有卖了。墟场上曾有过叉烧包卖,但后来发现是用死人肉做的。
曾经有过一段「看饼的日子」。那时饿了,便到茶楼柜枱上看饼,那里的叉烧包和萨骑马早已消失,换成形形式式的杂粮馒头,还有掺杂着米糠或稻草做的「高级饼」。有些要六角钱一个,相当于大姐一天的工资,所以每次都只能啜着口水,依依不捨地离开。白天看多了,晚上做梦也是父亲带我去茶楼,但吃了半天都吃不饱,醒来更饿,便哭着对妈妈说:「妈,我要吃叉烧包,我要吃萨骑马。」妈搂着我说:「仔仔乖,现在买不到叉烧,家里也没有油…..。」不知从甚麽时候起,妈妈已不叫我「云吞」,其实我瘦得更像「面条」。哭着哭着便停了,因为妈妈的泪水也滴在我脸上,「孩子」,妈说道:「妈想办法给你做萨骑马……。」
过了些时候,在香港的舅父寄来了几磅花生油,虽然打税很重,妈还是拿了回来,并在我生日那天,真的做起了萨骑马。没有面粉,便用番薯粉代替,加水搓成粉团,并压平切成小薄片,然后用油炸脆,捞起后把油彻底沥乾,再把「古巴糖」和成糖浆,淋在上面,便成了我盼望已久的「萨骑马」了。
糖浆尚未沥乾,我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味道简直比茶楼的要好上一百倍。但吃着吃着,便感到这东西的顔色和味道与茶楼的萨骑马不一样,便对妈妈说:「妈妈,这不是萨骑马嘛,是甚麽东西啊﹖」妈见我吃得开心,便说道:「这不是萨骑马,是妈做给你的生日礼物,叫’萨骑牛’。」当时母子俩笑成一团,难得高兴了半天。
不久,由于贫病交加,母亲不幸去世了。失去母爱的日子,就像寒冬中没有了太阳,童年的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母亲做的「萨骑牛」还留给我一些甜蜜、温暖的回忆。长大后,直至来到美国,我却没有去重做一次「萨骑牛」,因为我知道,「萨骑牛」,并不会比「萨骑马」更好吃,一个人的感受会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人的一生中会吃过无数的食物,但能像岛屿一样存在脑海中的恐怕不多。食物也许和事物一样,如人们常说的:「往事只能回味」。但我更觉得,我们应该对那个只能用「萨骑牛」,代替「萨骑马」的年代,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
我永远怀念在那苦难的岁月中,母亲做给我的「萨骑牛」。
(本文刊登于《世界日报》副刊)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