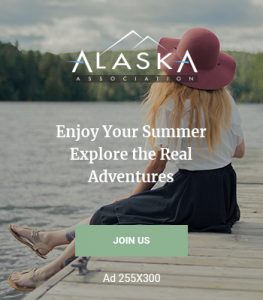凤凰城 崔增祁
我走进了当年生活的那块地方,这是一块”坝子”。云南人通常把一块平坦的髙地叫坝子,这坝子上是原资源委员会明良煤矿的员工的生活基地。我站在这块红土和石块凝成的土地上,往事涌上心头,艰苦但快乐的童年生活历历在目,那是一些永世也忘不了的故事。我的记忆中,两排长长的士坯堆砌的平房,住的都是由内地迁来的职员,房屋的西端尽头有一个销售生活用品的合作社和缝纫社,东端有一亇城堡式的大门,中间有一个烧开水的老虎灶和一个小歺厅,这是一个独立于当地居民之外的居住区。如今原来的房子都已不复存在,只有一户人家新盖了二层楼的房子住在这里。在我家住的地方只看到了那后边山坡上砌的石护墙,一眼看到那护墙上的石块,就觉得那么熟悉,似乎昨天才见过那样。人的大脑怎么会那样神奇,七十年了,怎么这几块石头的模样还会在脑海里,我従来没有像记英文单词那样去刻意地记过它。那石墙是我小时矦喜欢做冻豆腐的地方。每当冬季最冷的时矦,屋檐上挂起细细的冰柱,我就会在晚上把一块豆腐放在碗里,再加上一点水,第二天早上把一块冻豆腐交到妈妈手里。在这个坝子里,我还学会了生火炉,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拎起家里的炉子到老虎灶点燃几块煤,点着炉子后等妈妈回来做饭。为了改善生活,爸爸在对面的山坡上养了一隻羊,有时我还跟着爸爸去挤羊奶。我还曾在山坡上开垦了一块地学着种土豆,因为生物自然退化的原因,收成的土豆一年比一年小。这种田园式的生活堷养了我勤劳吃苦的精神,而坝子里的集体生活又给了我从小喜爱接触社会的特性。因为孩子不多,许多人是单身,我就成了社区的公共儿子,无论走到那里都受到叔叔阿姨的关心和爱抚,人们总是笑脸对着我,摸摸我的头,或是抱抱我,或是给我点吃的东西,我也时时以笑容相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欢笑。我爸妈很善待朋友,几个单身男人常常来我们家作客,妈妈的江南菜做得特别好吃,有一位叫胡伯恳的伯伯,几乎常在我们家吃晚饭,是我父母的挚友。在我工作以后,还受到父母的老友们给我的许多关照。童年时代的这段生活对我的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欢乐平和的环境里,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坦诚而纯真的对待周围发生的事。也许我父亲看到了我的弱点,在他离开人世前,留给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字幅。

七十年前小狗和我在家门口的像片
战争时期山沟里的文化生活十分缺乏。那时还没有电视,也看不到电影,更不用说看演出了。于是矿里的职工组织了京剧社,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社的票友,我也自然成了小票友了,每天淸晨我们都来到一座山谷里吊嗓子,听着山谷里的回音在耳边迴荡。我们一家人还全家出塲演出了”桑园寄子”。这些年到了耆英会合唱团,人们说我的嗓音不错,中气很足,问我是否受过专业训练,我无以为答,只说是爹妈给的,其实这根底可能受益于那个年代的吊嗓子。我现在能够哼唱的不那么准确但还能勉强入调的”借东风”和”武家坡”也源自那个时期。
我还想起了一件难忘的故事。当我七岁的时矦曾在这里自己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婚礼。一天,大人们都去上班了,我和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陆丽文(就是我上期提到的请云南省侨办邦助寻找的儿时的朋友)决定举行婚礼。于是我把妈妈平时用的化妆粉盒和胭脂口红都拿出来擦在她的脸上,擦得满脸红彤彤的,把家里办公桌下边的空间当作洞房,俩人蹲在底下举行了婚礼。我妈妈下班回来看到后,气得把我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其实我妈心里也挺喜欢这位”媳妇”的,只是心疼我把他的化𥺁品都用光了,而且办得太早。当我后来读郭沫若自传时,看到他寪到他在十三岁时摸着他嫂子的柔软的手, 心中顿时有一股异样的感觉,似乎从那时起,他有了对异性的要求。而我这次婚姻竟然比郭老提前了六年,实在是荒唐!不过那只是一塲儿童𨔼戏,真正对异性的感觉还是到了郭老说的年龄才出现的。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