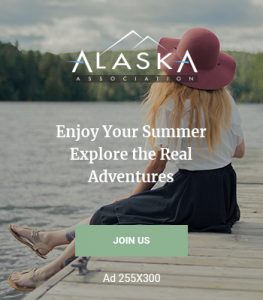凤凰城 丁丁
记忆总是和自己开着不适当的玩笑:当需要时它总是随着时光被渐渐淡忘;而想要抛开它的时候,它又突然跳出来,像个古怪的精灵,用针不停扎着我的心口,提醒我那些在大脑中刻下的痕迹有多深。
这一刻,我无法入眠-只因为知道了费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和他有三年未见,也没有打过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他,也包括他们全家亲人般的感情。我知道他和我在这点上完全一样,总是懒于和老朋友联系。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是对我们这种懒惰状态的最好托辞。然而这湾淡淡的水被他辞世的消息打乱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潭清水也可以有如此的深度。和听到消息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能做的就是在网上不停地查找更多的消息。网上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们的悼念之词,也说着他在学校教书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还有他大学时候的趣事;看着看着,那些和他在亚利桑那共处的无数片段,就如同被风翻开的书本,在我眼前把两年曾经的经历一页页闪现。
说是”老师”,只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叫他,我心里却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老师,坦率地说,我只把这个”老师”当作他的另一个更容易叫的名字而已。毕竟他的全名”费剑平”叫的比较拗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屋前一边踱着步一边吞云吐雾,一副很悠闲享受的样子,给我一副完全的背影。等他回过头来,我就看清了他的样子。
那一刻,就是那一刻。现实和记忆的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的我完全不能把他和病床和肝癌这种事情联系起来。然而当时光处在那一刻的他,活生生的他,转回身来,对我点了点头,憨憨地笑了笑。
浓眉、大眼、高鼻子、高个子、宽肩膀 -他长得应该绝对符合标准古典的审美。然而略为方正的下巴和满腮帮子的胡子茬让他和那些影视里精巧的帅哥分道扬镳,更不用提他当时壮硕得有些臃肿的身材和憨厚的笑容,让他讨巧地挤入了普通人的行列。肥大的套头红色运动衫勉强遮盖了他的腰围;所以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双手。和细小的香烟比起来,他的手非常粗大,几乎给我天天干农活的印象。我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于是,我和这个名叫”费老师”的人,就这么相识了。
我和他的关系一开始严格来说只是邻居。在美国这样的地方,邻居可以只是邻居,和国内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邻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完全地变成了我的另一个家人一般;更确切地说,他们全家和我家都变成了一家人。这种转变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我们住的公寓和他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我们只要不是工作的时间,有事没事就从我家跑到他家 ?然后再从他家跑到我家,如此周而复始地构成了我们简单的循环。时间久了,我会觉得我家的居住面积平白增多了一倍;而家人的数量也翻了一番。我和他的接触和网上写得最多的截然不同,是全然生活化的,没有一丝学术气氛和任何的师生关系;哪怕我折腾我的半导体材料他研究他的计量经济学,我和他共同的话题依然是面食和NBA居多。他对面食的爱好和我臭味相投;但是却完全没有我对于美食的起码要求。就本质上来说,只需要一大碗酱油辣椒拌面条,加点葱花,就足以让他动筷子之前说一句:”真香哪”,然后吃完后放下筷子再说一句:”真好吃啊。”我对篮球并不精通,仅仅能够勉强分得出乔丹和奥尼尔的差别。而他对于NBA的球队特点却娓娓道来,一场比赛中听他的评论,对我来说好像油炸花生米一般地香甜,让我很难得地和他一起坐在电视前多看了不少场比赛。当然,过程中他会时不时调调电视天线,力图增加电视图像的清晰度 -虽然往往徒劳无功。他对我的爱好之一围棋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很明显他完全只是初学的水平,和我下过一两盘之后,他就把对围棋的爱好完全局限在和电脑程序对战之中,绝口不提和我再战的事情。
在美国读书或进修过的人大概都会知道,那段时间的生活总是匆忙的、临时的。每逢有人搬家,费老师照例是一定被抓的壮劳力;当然,他帮助别人也是心甘情愿。我们住的公寓也谈不上条件有多好,家具更是东拼西凑。但是费老师在这样的状态里照样过得其乐融融。他有时候会一边大碗吃面,一边说起小时候没地方去睡大马路,饿着肚子吃不饱饭,然后一副满意极了的神情继续往嘴里吸着面条。当然这里也有他无法忍受的东西,那就是蟑螂。曾经有一次费老师往家里新添了一个大沙发(是旧的),然后他家里开始小强横行。对于杀蟑药这种化学生物制剂,尽管他没有在言辞上有所微词,但是他还是用行动充分表现了他的不满。有一段时间,每天见到他,他的眼睛都是肿的。一问,原来他每天夜深人静,都会突然起身,打开厨房的灯,然后对他视野所及的所有活体动物采用物理攻击;有时候一整晚甚至行动多次,于是他每次所能歼灭的数量日趋减少。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蟑螂的数量始终没有接近他满意的程度,于是他在狠动了一番脑筋之后,把那个新添的沙发解剖了一遍。那次的盛况我没有亲眼目睹,不过据他亲口说那次他快要达到了百强斩的程度。在这之后,蟑螂的数量最终下降到他能够忍受的地步,而他也终于能够心安理得的好好睡觉了,重新在脸上写满舒适的表情。
刚开始相识那段时间,Kevin(费老师的二儿子)还没有出生,我的孩子还小,所以已经能和大人们对话的壮壮(费老师的大儿子)也绝对是每天生活的主角。每次我到他们家里,经常的情景是春霞(就是学生们说的师母)在厨房,壮壮在看”花木兰”或是”狮子王”,而费老师在一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前工作。他的桌椅和他的身高并不很搭配,导致他得猫着腰看着屏幕;和他硕大的手指相比,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显得无比渺小,形成强烈的反差;而旁边几页纸,一支笔基本也只是摆设,大概100%的草稿都在他的脑子里。当然,大多数人也许无法想象,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在迪斯尼动画片的伴奏下完成的。如果我赶上这样的场面,我照例会坐下和壮壮一起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当然我偶尔也瞅过他的电脑屏幕,哪怕我对于半导体物理、量子力学和光电技术有些浅见薄识,但是满屏幕的符咒般的计量经济学的天书让我立刻捡起”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在等着吃饭的同时继续我的动画之旅。当然我也带费老师到我们实验室参观过,看着他对我们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一脸的诚惶诚恐,我的心里也在暗暗偷乐。费老师如果从工作中回过神来,经常会和壮壮玩”爬树”的游戏。他抓着壮壮的手,接着壮壮踩着他一步步一直蹬到胸口,接着一个后空翻落地。这个游戏我第一次见的时候目瞪口呆,但不久我也偷师成功,学会了这个危险度颇高的父子体操。
日子一天天过去,后来Kevin也出生了,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更加其乐融融。当然要说最高兴的还是一起出去玩。我们开着两辆旧车,把凤凰城附近的风景都扫描了一遍。当然开车的时候,照例是我痛苦地跟在他的车后面。而费老师开车有个显著的特点:只要一握方向盘,似乎就再不愿意踩刹车;每次出行的时候似乎对他来说都是公路拉力赛专门时间。有次去Canyon Lake(峡谷湖),在山路上蜿蜒盘绕,他在前面一骑绝尘,我在后面紧跟慢赶,手心和脑门全是汗。到了目的地之后之后两腿直发软,看着壮壮、我儿子,还有费老师托着Kevin在湖边的草地上高兴地一圈圈打转,我脑袋里也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一圈一圈转,然后我倒在草地上就沉沉睡过去,比在家里的床上睡得还香甜。另有一次我们租了辆大车去圣地亚哥,我和费老师换着开车;我当时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不用跟在费老师的赛车后边痛苦地追逐了。我两人开的是夜车,而车后三排座上,先是三个小孩子呼呼大睡;过一阵两个母亲也呼呼大睡。我们俩在前面一边聊一边开车,从理想、事业一直聊到哲学。到现在,那次在圣地亚哥玩的事情倒是印象有些淡了,但是和一起费老师开夜车的事情倒是记忆犹新。
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等费老师一家真的收拾行囊开始准备回国时,我们还高兴地谈论着将来。可是等离别的一刻真的来到时,我们只能强压着忧伤,而所有女士们的眼泪都多多少少地有些控制不住。送行,挥手,看着他们步入机场 -但是这些远比不上他们真的离去,而我却下意识地又朝楼上走去 ?隔着窗户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时,才知道费老师再也不会用他的大手托着Kevin牵着壮壮走在我们身边了;那种心理空空的感觉,竟然没有言辞可以形容。
那一刻都已过去。在这一刻。我在电脑前,絮絮叨叨如老太太一样,不知所云地说着一些事情。事情是关于一个名叫费老师的人,一个和我相处短短两年的人,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更是一个我永远的家人。和有些亘古不变的事物相比,生命也许本来短暂,就如风雨中的火苗,扑扑闪闪,不知何时就会熄灭。佛家谈到肉体的生命,不过是一幅皮囊;但是皮囊不具,魂归何处?这一刻的费老师,与我们已天人相隔,再见面也许不知是不是下个生死的轮回。如果那一刻我和他还记得前世,我会告诉他,春霞,壮壮,Kevin,我们一家,他的老师们,他的学生们,还有这个世界上星星点点无数的人无数还燃着的火苗,都很想他。
星抛满野夜无终,
烧酒噎喉凉如冻。
隔江掷杯泪成瀑,
对岸当歌舟已空。
丁丁 2010年2月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