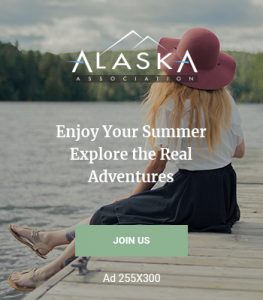父亲先是杨宪益先生的学生﹐然后又与杨宪益先生同事几十年﹐我们在家裡一直称他做杨伯伯。
杨宪益先生一九四0年英国留学归来后﹐就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教一年级英文。当时重庆中央大学一年级﹐不在沙坪坝中大校园裡﹐而在一个叫做柏溪的分校。因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佔领上海租界﹐暨南大学内撤﹐我的父亲辗转而到重庆﹐一九四二年进入中央大学﹐直接入读二年级﹐所以并没有在柏溪分校读过一年级﹐没有听过杨宪益先生的课﹐但既是中大学生﹐仍然要算是杨宪益先生的学生。
当时父亲就曾听说﹐杨宪益先生教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把《儒林外史》翻译成英文﹐使得父亲非常的敬佩。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做此事者不仅英文要好﹐更首先必须国学底子深厚。如果读不懂中文原作﹐翻译只能是胡说八道。由於家教关系﹐父亲自小研习国学﹐深知其渊其博﹐中国人裡十之八九不过略知些皮毛而已﹐特别是学外文的青年﹐精力都花在外文上面﹐顾不得其他﹐结果对中文更是一窍不通。近年父亲有机会讲课时﹐总是反复告戒学外文者﹐注重学习中文﹐杨宪益先生是最出色的例子。
杨宪益先生一九四三年就离开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到重庆北碚梁实秋先生主持的国立编译馆任职去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发现﹐中国并非天下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世界上除中国之外﹐还存在著许多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种﹐而且很多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比中国更加强盛之后﹐中国的外文翻译工作﹐就一直注重把外文著作译成中文而已﹐至今似乎仍然如此。但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梁实秋先生就想开闢一个反向领域﹐把中文经典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到世界上去。而行此事﹐无出杨宪益先生之右者。
杨宪益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的妹妹杨静如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一九四二年﹐我的母亲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同杨静如住同一宿舍。母亲虽然低杨静如两班﹐但成了好朋友。听母亲说﹐杨静如在大学裡﹐一直把母亲叫做陶陶﹐很特别。那个叫法﹐我觉得很好听﹐很有文学味道。杨静如后来到欧洲留学﹐归国后用笔名杨苡发表文章﹐成為著名作家﹐解放后在南京大学外文系做教授。我们至今仍然称她静如阿姨﹐改不过来﹐就像杨静如阿姨的女儿﹐至今仍然称呼我的母亲陶陶姨一样。
杨静如阿姨在中国﹐不是个陌生的名字。现在流行中国的一本译作﹐英国作家勃朗特写的《呼啸山庄》﹐就是杨静如阿姨译的。勃朗特姐妹﹐是母亲特别鐘爱的英国作家﹐我相信她与杨静如阿姨在重庆中央大学时﹐肯定同是勃朗特姐妹迷。我小时候﹐家裡的书架上放满书﹐其中有《呼啸山庄》的中译本。记得小学时读过一次﹐不大懂﹐中学时又读一次﹐懂得多些。接著就是文革乱起﹐红卫兵几次抄家﹐家裡带字的纸张全部毁灭﹐那本《呼啸山庄》也不得幸免。最近﹐我请杨静如阿姨签字送我一本她译的《呼啸山庄》﹐因為我曾亲身面临过魔鬼﹐确实的晓得恐怖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读起来自是另一番滋味。
静如阿姨曾对我讲﹐她自己已经大学毕业﹐而且结了婚﹐母亲才读大学三年级。静如阿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匆匆跑到医院来﹐找静如阿姨密谈﹐原来是我的父亲向母亲求婚了﹐母亲不知该怎麼办﹐只好找静如阿姨商量。结果当然显而易见﹐所以我有了这样一对父亲母亲。可惜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她们之间的通信来往就减少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越搞越烈﹐两人就断了联繫。只有杨静如阿姨讲陶陶的故事给她女儿听﹐母亲讲静如阿姨的故事给我们听。
文革之后﹐杨静如阿姨同我家终於恢复了联繫﹐可惜母亲已经不在了。杨静如阿姨听到噩耗﹐非常难过。直到如今﹐我从美国给她打电话﹐每一次她都要重复讲﹐一九七二年她刚从牛棚裡出来﹐到一个中学教书﹐同年杨宪益先生获释出狱﹐於是她就跑到北京会见哥哥。她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千方百计打听母亲的下落。虽然杨宪益与父亲都在外文出版局﹐但是从文革开始﹐杨先生坐了四年监狱﹐父亲则蹲了更多年的牛棚和干校。在当时残酷的社会状况下﹐正常人相互之间都不敢来往﹐更别说被关押和打倒的?#21453;革命?#12290;杨宪益先生如果到外文局找人打听沉苏儒﹐恐怕马上要被质问﹕问他干什麼﹖反革命勾结﹖说不定又要把杨先生关监狱﹐或者干脆把杨先生和父亲一起关监狱。
虽然刚从牛棚受苦受难出来﹐到了北京﹐终於自由﹐吃喝不愁﹐同修养一般﹐但杨静如阿姨不满意。除了没有找到母亲的失望之外﹐她也受不了北京城裡的那套虚偽和欺骗。杨宪益先生出狱﹐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英国家人都赶紧跑到北京来﹐了解杨先生的情况。西方人到底也弄不明白﹐中国人為什麼那麼仇恨文化﹐那麼残暴地迫害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杨宪益先生从阶下囚﹐摇身变成大花瓶。天天出入厅堂宾馆﹐坐席吃讌﹐政府官员日日簇拥前后﹐喜眉笑眼﹐讲述中国之伟大﹐中国人民生活之幸福。似乎杨宪益先生无辜坐牢的冤案﹐杨静如阿姨无辜蹲牛棚的迫害﹐不值一提。不仅不值一提﹐甚至好像根本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中国﹐普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就居然如此的低贱﹐如同牛羊一般﹐可以任意宰割﹐屠夫们连眼都不必眨一下。
因為这样两层关系﹐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以后,父亲跟杨宪益同事,经常来往。母亲有时也会跟父亲同往﹐谈谈杨静如近况等等。一九五三年成立外文出版社﹐杨宪益先生从南京调入北京﹐父亲从上海调入北京。杨宪益先生在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中国文学》杂誌任职﹐父亲在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人民中国》杂誌任编辑。据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刘尊棋先生化了很大力气﹐才调到他手下工作的。刘尊棋先生当年的雄心壮志﹐是把外文出版社办成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麼规模的出版社﹐对外介绍中国文化。
记得有几年﹐我常去外文出版社父亲的办公室,见过杨先生好几次。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带我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几次﹐那时杨先生住在西城百万庄外文出版局的宿舍楼﹐是一个普通的公寓单元﹐虽然比起外文局一般干部来﹐面积稍微大一些﹐但还是小得可怜。特别是杨先生家裡﹐四壁立满书柜﹐再加沙发﹐屋子裡面可以让人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我记忆里,父亲带我走进去﹐屋子裡并不明亮的,杨先生坐在屋角的沙发上,几乎像是蜷在裡面,旁边的茶几上放了几本打开的书。杨宪益先生当时瘦瘦的,抽著香烟﹐有一点无可奈何的神情。记得杨夫人戴乃迭﹐倒是蛮高大,朗声说笑,给我们端茶送点心﹐很像尽职的主妇。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戴阿姨给我们端来一盘金黄的桔子﹐非常甜﹐我从来没有吃过那麼甜的桔子。
那时期﹐中国还与世界隔绝﹐北京城大街上很少见到金髮碧眼的洋人﹐但外文局裡还是可以经常遇见﹐外国专家局裡当然外国人更多﹐所以我到杨宪益先生家﹐看见戴乃迭女士﹐并不觉得奇怪。而且他们夫妇两人﹐确实非常融洽和谐﹐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丝毫不让人感觉他们中间﹐一个是中国男人﹐一个是英国女人。
照我的家教﹐大人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小孩子只能坐在一边听﹐不许随便插话。所以我听父亲跟杨宪益先生交谈﹐实在没什麼意思﹐何况他们大多时间都是讲英文﹐我那时才小学生﹐一个英文字也没学过。戴乃迭阿姨忙过之后﹐也坐下来﹐参加谈天﹐那就更是全盘英文了。
父亲跟我说﹐他同杨宪益先生特别有话讲﹐是因為他们对翻译有相同的看法。几十年来﹐父亲一直遵从严复先生的翻译理论﹕信达雅。近年父亲还写作了一本翻译理论专著﹐书名就是《论信达雅》﹐此书由上海和台湾两家商务出版社出版。杨宪益先生也是同样的看法﹕翻译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必须儘量重视原文﹐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翻译第一要义﹐是信﹐译文不能离原文太远。当然光信不达﹐译文没人读得懂﹐也不行﹐但不能為了达而忽略信。至於雅﹐那就全看译者的文化修养了﹐外文中译能做到雅者﹐已属凤毛麟角﹐而中文外译能做到雅的﹐可说杨宪益先生之后﹐无一来者。
记得有一次从杨宪益先生家出来﹐父亲笑著对我说﹕他发现自己同杨先生的第二个相同之处。杨宪益先生自小在家裡读私塾﹐难怪他国学底子那麼好﹐直到十二岁才到外面读教会学校。可是他从来不肯用功读书﹐每年考试都是第二名。很多人劝他﹐只要他稍微多用一点心﹐就可以考第一﹐可是他仍旧总考第二名﹐从来不去考第一名。父亲在浙江省立二中初中毕业时﹐是全校第二名。后来参加上海市普通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又是第二名获雋。所以父亲说﹐他和杨先生是第二名阶级。不过父亲说﹕他自己还是很用功读书﹐很想考第一名的﹐只是没有考到﹐不敢跟杨宪益先生比的。杨宪益先生是根本不把考第一名放在眼裡﹐绝不肯用功去争取第一名﹐所以才考第二名。
我印象裡﹐杨宪益先生讲话声音并不高﹐也没有举手投足的大动作﹐十分沉静。可父亲说﹐杨宪益先生确是典型的文人,而且是个风流才子﹐与人交谈,几口酒喝下,便会海阔天空,才华横溢,出口成章。虽然不敢说他也能斗酒诗百篇,喝几杯酒﹐吟出个把篇来,是很经常的。父亲常感叹说﹕杨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没有逢到盛世﹐辜负了他的才华。
同许多中国学者文人一样﹐查阅杨宪益先生的官方生平﹐也跳过二十餘年空白﹐那生命的浪费﹐精神的苦痛﹐可以想见。期间﹐父亲同杨宪益先生的来往也断绝了。我只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杨宪益先生又回到《中国文学》去工作了﹐他竟然敢公开讲﹐刊物裡的文字﹐包括小说、诗歌、评论、文章﹐全是垃圾﹐毫无价值。父亲说完﹐摇摇头﹐笑了﹐补充﹕到底还是杨先生。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