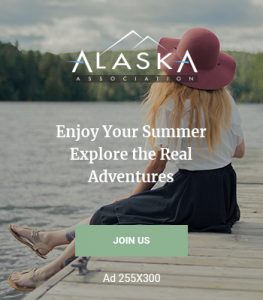我从小就经常替父亲母亲抱不平﹐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人﹐只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有个西南联大﹐是好学校﹐却不知道重庆有个中央大学﹐也是好学校。我的父亲母亲是中央大学毕业﹐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说出去不响亮。特别是我母亲﹐曾经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为与家人团聚﹐转学中央大学而后毕业于此﹐把朱自清学生的名头也丢了。
西南联大是好学校﹐自不必说﹐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间名校的合并。那之前﹐我的外祖父曾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和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中央大学也是一间好学校﹐先在南京﹐后到重庆﹐因为一直地处国家首都﹐故称中央大学﹐现在改叫南京大学。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前﹐我的外祖父也曾做过中央大学的教授。我想之所以一九四九年后中国人不多提中央大学﹐是因为抗战期间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由蒋介石任校长。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经常连孩子带澡盆一起扔掉。
我的母亲一九四0年在香港培道女中二年级﹐以同等学历考取昆明的西南联大﹐却因战时交通阻隔﹐延迟至一九四一年才得以到校入学。她自幼热爱文学﹐读书写作教授曾是她的梦想﹐所以进西南联大以后﹐读的是中文系。她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讲﹐她在西南联大时﹐听过朱自清的课。她写的文章﹐也由朱自清亲笔改过。
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城里猛烈批判三家村﹐吴含(左加日边)邓拓廖沫沙。母亲经常摇头﹐对我说﹕吴含(左加日边)先生是非常好的历史学教授。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只要吴含(左加日边)讲大课﹐她一定要去听﹐而且要早去讲堂﹐才有座位。每次吴含(左加日边)的大课都会超满﹐去得稍晚﹐就得挤在人群里站着﹐经常还有男学生爬到窗台上坐﹐景象很热烈也很壮观。吴含(左加日边)讲课所以那么受学生欢迎﹐不仅仅因为他博学﹐演讲有激情﹐而且因为他总是站在一个独立知识份子的立场﹐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权者。古今中外﹐凡有学识有思想的知识份子﹐都以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为荣﹐而母亲读书那时期的学生﹐也是受那种教育长大的﹐所以特别喜欢吴含(左加日边)那样的教授。
我听着母亲讲的各种过去教授故事﹐总会特别地羡慕母亲。她曾经上过那么多名教授的课﹐而我那时则连读大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梦。
很奇怪的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历数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所听过课的名教授时﹐不止一次提到过马寅初先生的名字﹐而且对马老表示极度的尊敬﹐对他后来几十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愤慨。母亲认识马寅初先生﹐是可以肯定的﹐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马仰兰曾在重庆中央大学跟母亲同班﹐后来又同事。可母亲在西南联大或中央大学读书时﹐马寅初先生是否在两处讲过课﹐却未可考。
根据目前中国大陆可以读到的官方资料﹐马寅初先生因一九四0年公开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演讲﹐惹恼蒋介石﹐遭军警逮捕﹐关进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一九四二年获释后﹐继续被蒋介石软禁。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六年中﹐没有关于马寅初先生工作及生活的体史料的公布﹐不知他那时是否在西南联大或中央大学讲过课。
台湾资料里很难找到有关马寅初先生的记载﹐而中国大陆关于马寅初先生的资料﹐这一段时间总是略带一笔跳过﹐很不详细﹐甚至互有矛盾。比如有的说他一九四二年获释﹐有的则说他一九四四年获释。有说他从一九四0年起﹐被监禁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四年的﹐而后继续被软禁重庆歌乐山上。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人﹐都知道重庆歌乐山是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所以此说似在暗示马寅初先生被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可是一九四四年马寅初先生确出版了一本专著《通货新论》﹐他什么时候写的﹐又在哪里写的呢﹖
我听母亲讲马寅初先生故事的年代﹐无处获知马寅初先生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那个时期流行于世的官方说法﹐一律是马寅初先生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反毛泽东﹐恨不得说马寅初先生原本就是蒋介石心腹﹐哪里还会重提他曾被国民党下狱的历史。母亲没有对我讲过马寅初先生曾遭国民党逮捕﹐她也许不知道。从年代上看﹐她与马仰兰同学的时候﹐马寅初先生已经出狱。是否还被软禁歌乐山﹐母亲看来也不知道﹐因为马仰兰上学回家似乎很正常﹐母亲并没有感觉到她家有什么不自由。后来马仰兰阿姨给我写的信里﹐也提到当年许多同学单身到重庆﹐没有父母在身边﹐生活比较苦﹐言下之意﹐她有家在重庆﹐生活好得多﹐不像父亲那时被软禁的样子。
但母亲确实告诉过我﹐一九四九年以前﹐马寅初先生确以敢于公开批评蒋介石政权而著称于世﹐国民党对他是又恨又怕。我就不明白了﹐记得曾经问过母亲﹐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一直骂蒋介石独裁专制﹐无恶不做﹐马寅初先生那么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怎么他的女儿还能读中央大学呢﹖根据我自己当时的经验﹐只要家庭出身反动﹐子女绝无可能升学﹐别说大学﹐我认识的人里﹐许多子弟连中学都不能读。
母亲听我问这样的问题﹐微笑着沉默片刻﹐然后说﹐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是基本按照宪法执政﹐相当开明和民主的﹐并不像后来几十年所渲染的那样。二伯伯沈钧儒先生最反对国民党政府﹐整天在议会里骂蒋介石﹐外祖父还跟他做朋友甚至结亲﹐蒋介石碰也没碰过二伯伯一指头。还有章乃器先生﹐章伯钧先生﹐储安平先生﹐当年都是公开骂蒋介石独裁的好手﹐国民党没把他们怎么样﹐照样自由自在﹐日子过的舒舒服服﹐倒是后来共产党把他们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母亲讲过以后﹐马上补充﹕这话是家里自己讲的﹐出去不许乱说。
有一次谈及这些﹐她叹口气说﹕如果那时像现在这样子﹐马仰兰是无论如何不能读大学的。我知道她是在为我们三个孩子难过﹐我们没有马阿姨那么幸运。我读中学时﹐中国发生文革﹐大学都不召生。七十年代后﹐有些学校召工农兵学员﹐弟弟在内蒙改造表现好﹐被农垦兵团推荐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最后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北大除名。一九七七年大学恢复高考﹐我和弟弟同时参加﹐成积都高过北大录取线几十分﹐可是因为家庭出身的政治问题﹐北京大学又一次把我们兄弟二人抛弃了。
我相信母亲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她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我们讲真话﹐而且母亲因为不肯做昧良心的事﹐受了几十年政治迫害﹐可她到底还是不会讲假话。但我仍然很多年无法证实﹐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究竟是独裁还是不独裁。一九七九年马寅初先生被官方”平反”了﹐于是中国大陆有关马寅初先生的历史资料就渐渐公布出来﹐特别反复强调他当年被蒋介石逮捕的事情﹐极力把马寅初先生描绘成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大英雄。
虽然我对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非常不耻﹐不过我倒也从这些资料里﹐证实了母亲对国民党政府的总结。根据中国官方资料﹐马寅初先生从一九四0年到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或软禁﹐但显然那期间他在继续读书写作﹐还在被监禁期间(一九四四年)公开出版新著作。也是他还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重庆各界公开集会庆祝马寅初六十大寿﹐并没有被国民党指控为反动集会﹐也没有遭到警察局的禁止或者破坏﹐更没人因此被捕。对比马寅初先生后来二十余年的经历﹐他在重庆期间简直是太自由了。再比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被关押的文化名人的命运﹐马寅初先生那时简直生活太幸福了。
有一点我很存疑﹐就是我的外祖父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有关马寅初先生的回忆。从年代上查对﹐一九一九年马寅初先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时﹐外祖父在北京大学读法学院。可在外祖父有关北京大学学生生活的回忆里﹐包括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有许多蔡元培校长的详细纪录﹐却从未见提及马寅初教务长的名字。顺便说一句﹐我所见到的其他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献﹐似乎也没有提到过马寅初先生的。一九二九年马寅初先生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而外祖父一九三0年初受聘为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在其回忆中仍然从无有关马寅初先生的纪录。若论起来﹐马寅初先生当时是中国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外祖父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派领袖﹐两人无论如何不至于互不相识吧。
到四十年代初﹐史料上记载马寅初先生被蒋介石逮捕的时候﹐外祖父刚脱离日寇魔掌﹐逃出香港到达重庆﹐所以应该并不知道有那事发生。但不论马寅初先生获释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四年﹐那时外祖父已经进入蒋介石的权力核心﹐并且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碰上马寅初先生那样响当当的铜豌豆﹐继续到处批评国民党政府﹐外祖父绝不会无所知或无所为。可是遍查外祖父所有的回忆文字﹐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处提到马寅初先生的文字。
我怀疑是否外祖父其实很尊敬马寅初先生﹐我知道外祖父尊敬一切真有学问的人﹐可因为马寅初先生曾得罪过蒋介石﹐外祖父避尊者讳﹐所以不能讲他的好话﹐又不愿意讲昧心的话﹐所以干脆一字不提。可是在外祖父的回忆里﹐并不忌讳提及当年曾激烈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物﹐如郭沫若﹐许德珩﹐甚至中共领袖周恩来董必武等。外祖父在庐山会上﹐曾专门拜访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三人﹐并称赞他们言行温文尔雅﹐颇得众人好感。外祖父也曾具体地纪录了他在北平与延安代表凯丰先生的密谈﹐好像并无禁忌。
不过﹐不论马寅初先生与外祖父是否相识﹐相敬﹐或相仇﹐他们的两个女儿却是同学﹐同事﹐好友。也因为马寅初先生是母亲非常尊敬的人﹐马仰兰阿姨又是母亲异乎寻常的朋友﹐我们后辈甚至愿意尊称她做恩人﹐因为马阿姨在我们家受迫害最深重时﹐从美国回归而特别来我家看望过母亲。所以我们对于马老的身世特别关心﹐同时对于中国史界对马老生平所表现的选择性记忆﹐那么多轻率的忘却﹐那么多粗暴的歪曲﹐既理解也不满。
记得我还在小学时候﹐父亲母亲曾带我们三个子女﹐到北京大学去过几次﹐拜访他们的老师俞大因(左加丝边)教授。我想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因为我的母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就也不大敢同亲友来往﹐以免给别人添政治麻烦。一九五九年后母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六十年初父亲参加毛选四卷英文版翻译﹐似有受重用的迹象﹐父亲母亲才又带了我们重返北京大学﹐再访俞大因(左加丝边)教授。那时我已读中学﹐就记得很清楚了。
我记得一九五七年以前有一次去北京大学﹐拜访过俞大因(左加丝边)教授后出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走路﹐母亲忽然提出﹕我们是不是顺便去看看马老﹖好几年了﹐也不知仰兰情况如何。不记得父亲当时怎么作答﹐反正我们没有去看望马寅初先生。当时马老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也都听说他几次向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提出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
一九五七年血雨腥风﹐数十万知识份子做了阶下囚﹐母亲捐了门槛﹐也终于没有逃脱悲惨的结局。我们家里自身难保﹐也就顾及不到别人。但是我记得运动过后﹐母亲获知马寅初先生没有被划做右派﹐还是很觉庆幸。她说﹕马老那样的学问家﹐如果从此不能著书立说﹐那就太可惜了。但那只是母亲那种知识份子们的愿望﹐大批中共领袖所希望的﹐就是不让马寅初先生那样的学问家们开口讲话。仅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批判马寅初先生”反动思想”的文章﹐就有二百多篇﹐上纲上线﹐措辞激烈﹐恨不得将马寅初先生千刀万剐的架势。
凡中国人都知道﹐毛泽东个人极为痛恨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将之斥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翻版﹐所以才会有全国上下一片对马寅初的杀伐之声。后来几十年间盛传的”马尔萨斯姓马﹐马寅初也姓马﹐马尔萨斯是马寅初的外国祖父”﹐”马寅初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马寅初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马寅初不可手软”等等﹐都是毛泽东当年亲口讲出来的话。顺便提一句﹐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我读许多中国官方有关马寅初先生的资料﹐居然会堂而皇之地说﹐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曾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只是康生等人在迫害马寅初先生﹐这可真是太卑鄙﹐也太可悲了。
既然毛泽东亲下罪诏﹐马寅初先生绝对无翻身的机会﹐北京大学校长撤了﹐人大常委也撤了﹐中央并且具体规定﹐马寅初先生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就是说﹐马寅初先生在被国民党监禁之后﹐又被共产党软禁起来。国民党关了马寅初先生两年﹐共产党软禁了马寅初先生二十年。而且那年马寅初先生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就算仅仅出于尊敬长者的中国传统﹐也不该那么对待他吧。政治斗争实在是无人性可言﹐太过残忍。
那种高压状态之下﹐母亲还是曾经悄悄告诉过我一些马寅初先生讲过的话﹐记不清当时母亲所用的每个字﹐但意思后来证实还是真实的﹕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述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母亲当时转告马寅初先生这些话﹐不知是为讲给我听﹐还是讲给她自己听﹐增强她鼓足勇气度过难关的信心。
母亲没有讲过﹐她从什么地方获知马寅初先生讲的这些话﹐但后来从许多其他来源证实﹐都大致不错。从在中国政治旋涡里打转二十多年的经验﹐我可以想见﹐中央和上级经过挑选﹐把马寅初先生提交的某些报告中的只言片语摘出来﹐一级一级下达到全国各地机关或社会上﹐用以组织群众无情批判。马寅初先生早已是死老虎﹐继续批判又有什么意义﹖其实项庄舞剑﹐意在给批判者们心里制造深度恐惧﹐唯上级之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母亲则从那些被歪曲的引文中﹐获知了马寅初先生的心声。别人骂做死不改悔﹐母亲就理解成坚强不屈。别人骂做执迷不悟﹐母亲便解释为坚持真理。于是我们便也获知马寅初先生在那种非人的迫害下﹐始终没有屈服﹐我们对他是极为尊敬的。
我特别记得母亲转告马寅初先生的一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因为家庭出身的压迫﹐我自小就懂得夹紧尾巴装孙子﹐听任身边那些无知无耻之徒装模作样盛气凌人。但即使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仍免不了要经常写思想汇报或思想检查﹐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已经是人生最大的错误﹐就必须多写检查。自从听母亲转述马寅初先生那句话后﹐我就再不肯写思想检查和思想汇报了。也因此﹐进中学我入不了共青团﹐以后更入不了共产党。但我对自己说﹕我可以不做共产党﹐却不能不做马寅初先生那样的人。
马寅初先生一辈子受的冤枉﹐可谓不少。但是老天有眼﹐当初骄横跋扈的强人﹐一个一个都死了﹐而马寅初先生却顽强的活下来﹐而且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完结。一九七九年马寅初先生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大学做名誉校长。可惜我的母亲没有那么幸运﹐前一年因病不治。我相信如果母亲仍活着﹐她一定会带我去北京大学﹐拜访马寅初先生一次。
事实上﹐在北京许多年间﹐我们家住得离马寅初先生家不远。马寅初先生家住在东单东总布胡同里﹐我家刚从上海搬到北京以及文革后期﹐都是住在北帅府马家庙﹐跟东总布胡同只隔一条猪市大街。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建交以后﹐之后马仰兰阿姨终于得以回到北京﹐探望父亲马寅初先生﹐她从自己家走路到我家来看母亲﹐我也曾陪马阿姨走路﹐从我家送她回家。
母亲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同时也改了专业﹐从学中国文学改为学英国文学﹐进了英文系。据父母亲回忆﹐当时他们那一班﹐始于一九四一年﹐故称四一班﹐全班不到二十名学生﹐女生多于男生。后因政府在大学生里征募英文翻译﹐男生中有三人应征从军﹐到毕业时全班只剩四个男生﹐包括我的父亲和丰子恺先生的公子。班上女生许多出身名门﹐我的母亲算一个﹐另外还有丰子恺先生的女公子﹐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蒋百里将军的女公子﹐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女公子﹐青岛警察局长的小姐﹐无锡荣老板家的千金等。
中国很久以来就有一说﹐读大学的多出身书香门第﹐读英文系的更多是阔家子弟﹐都是准备将来出国留洋﹐然后归国做大事业。就当年母亲那个班看﹐此说似乎是很有些道理。我的父亲虽出身世族﹐但因祖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到他父母亲﹐就都只做小职员而已﹐那个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在中大英文系那个班里﹐就是最差的一等。
马仰兰阿姨五十年后﹐写信给我说﹐有许多同学(大多是男生)﹐只身赴重庆就学﹐父母都不在﹐他们的生活比较苦﹐好像就是靠政府发的一点生活费。我最记得你爸爸的一件事是﹐他似乎总是穿着一种灰色长袍﹐冬天把棉花(或丝棉﹖)塞进去﹐夏天又拿出来。至于你们的妈妈﹐有家在重庆﹐生活就舒服得多。
不弱于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也是师资雄厚﹐名家如云。仅父亲母亲所就读的中大英文系而言﹐就聚集了范存忠、楼光来、俞大因(左加丝边)、俞大缜、初大告、徐仲年、许孟雄、杨宪益、叶君健、孙晋三、丁乃通等学界大名鼎鼎的教授。
古所谓名师出高徒﹐中大英文系里﹐更是名师加高徒﹐可想父亲母亲在那个环境里﹐学习会是如何地刻苦﹐生活又是如何地幸福。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自己总结﹐她的一生苦难远多于快乐。而她生命中真正可算幸福快乐的﹐有四个时段﹕一是北伐战争后回到上海﹐她读小学的头几年。二是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她小学毕业进中学的那几年。三是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的三年。四是跟父亲结婚后在南京度过的四年。
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结交的朋友就有一个马仰兰。一九四五年夏初﹐父亲母亲那一班毕业。母亲由外祖父介绍﹐进中国农业银行研究室工作。父亲则经沈钧儒介绍﹐被刘尊棋先生录用﹐进了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就是现在美国新闻总署的前身。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父亲母亲的同学朋友马仰兰阿姨﹐也同时一起进入美国新闻处任职﹐跟父亲成了同事。
八一五光复﹐父亲马上被美国新闻处派往上海筹备新办事处﹐随后母亲辞去中国农业银行工作﹐跟着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初他们结婚以后﹐母亲在上海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找到一份工作。同年马仰兰阿姨也从重庆回到上海﹐就住在父亲母亲在狄斯威路的家里。然后也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找了份工作﹐又跟母亲成了同事。
但马仰兰阿姨那时并没有准备长期在上海工作﹐她已经联系好了美国学校﹐正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不久她就一切就绪﹐登船出海。母亲曾经对我讲过好几次﹐马仰兰阿姨出国的时候﹐是她和父亲两个人送到轮船上去的。那时父亲已经转入上海《新闻报》做记者﹐所以有一部黑色的奥斯汀汽车可以开﹐就把马仰兰阿姨连行李一起运到码头。后来父亲到南京做特派记者﹐另外有一部吉普车开﹐但在上海仍保留着这部黑轿车。我的弟弟出生﹐母亲抱着他照相﹐家门口背景还有那部汽车。文革期间﹐因怕被当做资产阶级生活证据﹐把人像留下而将背景上的汽车剪掉了。
母亲对我讲过﹐本来他们三个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都曾决心毕业后要出国留学的。母亲曾获得英国一所私立女子大学的录取﹐父亲也曾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录取。但是他们当时正处热恋﹐不肯一欧一美﹐远隔大西洋。而且父亲也没有那么多钱﹐出洋留学。所以最后两个人都不出国了﹐宁愿斯受上海。这情况下﹐马仰兰阿姨出国﹐自然十分引动父亲母亲的伤感。
父亲只好自我安慰﹐说是上海《新闻报》也许会到美国开设一个通讯处﹐那么他或可努力争取﹐被派到美国去工作一段时间。那么三个同学同事朋友﹐又可以在美国相聚了。分手的时候﹐他们庄重地约定﹐不论天涯海角﹐他们一定再见面。我至今仍能记得母亲跟我讲这段往事时的表情﹐神往而凄凉。
谁也没有想到﹐马仰兰阿姨的这个承诺﹐经过了三十年的曲折磨难﹐才终于实践﹐而两个老同学的再度见面﹐ 给母亲的心里造成多么巨大的震动。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已经跟不少亲友失去了联系。一九五七年母亲成了右派﹐更不敢跟别人联络。到了文革﹐我家被炒几次﹐父亲被关牛棚送干校﹐期间我家又被赶出旧居﹐几乎再也不会有人还找得到我们。但是马仰兰阿姨却找到了。她后来讲﹐中美建交后她头一次回国﹐便打听到父亲在外文局工作﹐可是没来得及打听出我家住址﹐便返美了。隔了一年再次回国﹐就决心打听出我家地址﹐从西城找到东城﹐终于成功。
我 清楚地记得马阿姨一九七四年头一次来我家的情况﹐我那时本已下乡陕北插队﹐刚好回京﹐所以碰上马阿姨。我们那时住在一个极破旧的小阁楼上﹐狭窄的木楼梯没有灯﹐黑洞洞的﹐所以马阿姨走上楼的脚步﹐犹犹豫豫,走一步停一停。我听到了﹐便开门出去。看到是一位中年妇女,瘦瘦小小,头上蒙一块花头巾,一副大眼镜占去脸的大半。她穿的那件半长不长外衣,那双淡黄色小巧玲珑的皮鞋,当时中国不生产。长脸,嘴唇很红,显然涂了口红。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是看不到的﹐我便猜她从海外来﹐但我并不认识她。
听说是马仰兰阿姨到了﹐母亲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张着两手,迎接她的朋友。她们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身体都在剧烈抖动。马阿姨的肩头上,母亲干涩的眼睛,流出不断线的眼泪,冲刷她布满皱纹而浮肿的脸。母亲说:你回来了,又见面了,真想你啊!马阿姨说:又见面了,二十七年了,我也真想念你啊。母亲说:很多年没人来看我了。马阿姨说:我答应过你,一定回来看你﹐可惜来得太晚了。母亲说:是,你答应过,我记得。再晚,我也等着。
听她们简短的对话,我心里难过得要命。马阿姨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绢,轻轻替母亲擦去脸上的泪,然后又轻轻擦去自己脸上的泪。母亲说:你万里迢迢来看我,我站不起来,不能招待你。马阿姨说:我们老同学,还讲客气吗?你们当年在上海,让我住在你家,待我那么好,送我到码头上船,就够了。我会记得一辈子。听了这话,母亲哇哇放声痛哭起来,张开两条弯曲的胳臂,搭在马阿姨肩上,猛烈抽搐,说:有人记着,有人记着。母亲一生,经受多少苦难,付出多少心血,蒙受多少冤曲,承担多少离别,她都无怨言。她只希望得到别人一点理解,一点尊重,一点记忆。
我悄悄离开母亲的屋子,给她们留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两个人在母亲屋里坐了一下午,没有叫过我一次。我在外面独自坐着发呆,羡慕母亲一辈人的真诚友情,也为自己这辈人的孤独和薄情而悲哀。
天暗淡下来,我送马阿姨回家。黄昏之中,我们走出院门。马阿姨把手插在我臂弯里挽着,边走边说:你母亲年轻时会唱昆曲,活泼得很。我们约好,她到美国去找我的。真没想到现在她会这样子。我说:”知道,天灾人祸。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马阿姨说:母亲常跟你们说她的往事吗?她有很多故事可讲。我说:”时候讲一些。我们这样家庭的人,都怕接触过去,太痛苦。”马阿姨说:你们应该记住母亲的一生,她是很伟大的女性。我说:我会永远记住。不是母亲,我们这个家早就没有了。马阿姨说:真可惜,她当年多么有才华,她立志要做冰心一样的人。
我心想,冰心自己在国内又怎么样了?还不是倒霉到家。然后我说:马阿姨,谢谢你今天来,姆妈可以吐一吐自己心里的感觉。马阿姨说:我懂。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她的欢乐,她的痛苦。我们再没说什么话,默默走到东总布胡同马老先生家门口,在苍茫中告别。我说:谢谢你,马阿姨,二十多年了,今天大概是姆妈最快乐的一天。马阿姨说:宁宁,请你替我好好照顾母亲。会有一天,她能够到美国来。她会看到她的父亲和弟弟们。我沉默着点点头,跟马阿姨道了别,独自一人走回家去。
隔了一年﹐马阿姨第二次来我家﹐我没有在﹐是妹妹接待的。后来她讲给我听﹐她送马阿姨回家﹐马阿姨请她进去坐了一坐。也许那时候普通中国人住宅都十分窄小﹐我家情况更糟﹐所以妹妹说马寅初先生家里大极了﹐走进去这里一间屋那里一间屋﹐好像在迷宫里。大概当时刚好马老的孙子们准备出国﹐几间屋子和走道里都放了箱子行李。几个年轻男孩子﹐奔来跑去﹐讲着带些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个个志得意满的样子﹐毫不理会我的妹妹。
我听妹妹这话﹐就想起来文革刚开始的期间﹐据说因为周恩来的特别保护﹐马寅初先生的家暂时没有遭多大殃。可是为了恐惧红卫兵的肆虐﹐马寅初先生的亲孙儿自己动手﹐把马老收藏数十年的大批文物古董﹐都偷偷堆起来﹐一把火焚为灰烬。那个故事在当时北京城里我们这些”反革命狗崽子”圈里﹐广为流传。当然谁也不敢传给高干子弟红卫兵﹐否则马家的公子们都得大遭殃。听到那故事﹐我为马寅初先生的不幸而伤心﹐对马家孙子的作为又十分理解。我绝不责备他们﹐只有我们同样家境的子弟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对方的悲痛。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得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自己也曾设法销毁掉家里保存的书画唱片﹐也曾想尽办法把外祖父刻了字留给母亲的一个墨盒丢进紫竹园的湖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三千年后在马寅初先生的家里﹐再现过一次。我能想象﹐马家的公子望着熊熊大火中燃烧的珍贵字画﹐心里会如何的无奈和痛苦。
而更永远铭刻在我心里的是﹐妹妹告诉我﹐她在马阿姨陪同下﹐走在那大房子里﹐左看右看﹐总想有个机会能够看一眼著名的马寅初先生。最后真被她看到了﹐通过一个走道的时候﹐她看见一间屋子里面﹐一个瘦弱老人的侧面﹐满头稀疏的白发﹐深驼着背﹐坐在一部轮椅车里﹐旁边空无一人。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孤孤零零﹐安安静静﹐没有声息﹐没有生意﹐完全好像一座白玉石的雕像。
妹妹相信﹐那一定就是马寅初先生了。她略略站了一站﹐心里挣扎了片刻﹐终于没有敢过去打扰他老人家﹐就轻轻地离开了。妹妹告诉我﹐她回家把所见讲给母亲听﹐母亲未及听完﹐就痛哭失声。母亲万万想不到﹐当年中国的第一教授﹐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的校长﹐居然会被折磨到如此地步﹐那确是人类最无可忍受的悲剧。同时那对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又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可惜的是﹐没有马寅初先生那样的文化思想水平﹐中国即使有十三亿人口﹐也几乎无一人能够了解他﹐而且不仅不能了解他﹐还要反过来迫害他﹐结果害了国家和后代。我想﹐马寅初先生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了。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