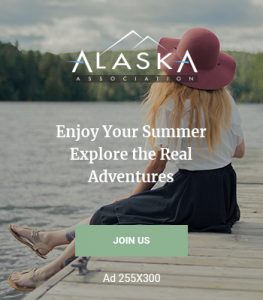抗战后期﹐蒋介石决定亲自署名写一本书﹐分析抗战形势转折和胜利前途﹐鼓舞中国人民的必胜决心和意志。这本书的撰写﹐便交由外祖父执笔﹐就是《中国之命运》。那段时间﹐外祖父每天上午晋见蒋介石﹐修改以前文字﹐商讨新写章节。中午外祖父回到办公室﹐便将蒋介石之口授写成文字。下午草稿完成﹐交随从用小楷抄清﹐同时外祖父就为中央日报写社论或者署名评论等。第二天上午﹐外祖父拿了随从抄好的文字﹐再去晋见蒋介石。
如此周而往复﹐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四十余天﹐日夜兼程﹐完成初稿。然后校阅排版﹐印刷二百册样书﹐交党政要员阅读提意见。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一介武夫﹐自协助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起﹐北伐抗战﹐率军近二十年﹐何曾听说他写过什么文章。现在突然之间﹐蒋介石居然说是亲自写出一本书来﹐不免让人生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猜出﹐那是其文胆陶希圣的文字。满重庆城里﹐到处是责问外祖父的喧嚣。
这之中﹐忽然一天蒋纬国跑到上清寺委员长侍从室﹐大步走进外祖父的办公室﹐举着一本《中国之命运》样书,连声说”写得不对﹐写得不对”。那时蒋纬国只有二十六岁﹐军衔不过上尉。却因为父亲是中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竟敢来责问中将军衔的外祖父。蒋纬国满面怒色﹐责备外祖父把自己的理念强加到他父亲的名下﹐致使党国元首遭天下人非难﹐憋住劲头﹐要对外祖父发一顿脾气。
外祖父在写作时便料到﹐书成之后定会发生这等事情﹐所以早有准备。他只是没有想到﹐最先打上门来的﹐会是蒋介石的小公子。他站在那里﹐等蒋纬国发过一阵火之后﹐不声不响﹐从上锁的办公桌抽屉里﹐一本一本拿出《中国之命运》的原稿,摊在桌上排列好﹐然后对蒋纬国讲:”这是全部初稿﹐请你仔细过目。上面每一页文字﹐都经过委员长亲自改写。大部分章节都曾改写过七八次﹐有些甚至改写过十几次﹐原封不动﹐都蒋纬国上尉站在桌边﹐一本一本翻看﹐过了好半日﹐几次的修改稿上﹐每页稿纸上﹐读到的都是父亲的亲笔手迹﹐也就无话可讲﹐悻悻地走了。
不过据外祖父说﹐蒋介石的这个小公子﹐其实人很和气。 《中国之命运》那次﹐大概是他唯一对外祖父发脾气的一次。其他时候凡他见到外祖父﹐总是很有礼貌﹐和颜悦色。特别是抗战胜利﹐国府还都之后﹐外祖父住在南京田吉营﹐蒋纬国经常独自跑来他家﹐跟外祖父谈天说地。那年蒋纬国二十九岁﹐升为中校﹐一九四八年他三十二岁﹐升为上校。到蒋纬国三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做了少将﹐但那是后话了。
一九四六年﹐我的父母结婚不久﹐父亲出国印尼南洋之后﹐一九四七年奉调任上海《新闻报》驻南京特派记者﹐专责国府政治要新闻报导。所以他们二人保留着上海狄斯威路的小洋房﹐以备回上海时小住﹐其他时间则在南京城左营的上海《新闻报》分社居住。那两年时间﹐是父母一生中最安静和快乐的日子。母亲在总统府任了个挂名秘书﹐职责是协助外祖父做些文书工作﹐很少往总统府报到﹐只需经常到田吉营外祖父家里去﹐而那恰是母亲最欢喜做的事情。
我的三舅那时刚入初中﹐才学会开车﹐正是万分着迷的时期﹐看见汽车手就发痒。父亲曾告诉我﹐那时为了跑新闻﹐报社给他一部吉普车﹐由他每天开了到处跑。所以他能够经常开了车﹐送母亲到外祖父家去。而凡到外祖父家﹐只要碰上三舅在﹐父亲前脚进门﹐三舅后脚就把他的吉普车开走﹐到明故宫或者中山陵去绕上几圈。
有一天蒋纬国上校又独自开了车﹐跑到外祖父家来谈天。三舅放学回家﹐看见门外停了一辆亮闪闪的军用吉普﹐心就跳起来﹐忍不住摩拳擦掌﹐过去摸了一遭。待他轻手轻脚进了门﹐看到是蒋纬国上校在座﹐那么门外那吉普车﹐显然就是将军的了。他见外祖父和蒋纬国两人边饮茶边谈天﹐兴致勃勃﹐完全没有马上结束的意思﹐便下决心开上校先生的车子去过一回瘾。
三舅放下书包﹐蹑手蹑脚溜出大门﹐一跃跳上那部吉普。蒋纬国上校到了外祖父家﹐车停在门口﹐连钥匙也不拔下来﹐三舅大喜过望﹐脚一踩﹐手一转﹐车子发动起来﹐眨眼之间﹐就开出了街。三舅洋洋得意﹐左抡右闪﹐在马路上风驰电掣﹐没几下子就到了常去的中山陵。不料这一次﹐他还没绕过几圈﹐就被值勤宪兵拦住﹐问他是什么人﹐开车在这里做什么。三舅那时虽然只是个中学生﹐但自己心里也晓得﹐不管是不是犯了什么路规﹐那无照驾驶一条﹐已经够麻烦了﹐所以很害怕﹐紧张得讲不出几句话。于是宪兵便把三舅连车子带人一起﹐送进宪兵队总部查问。
原来蒋纬国上校开的车子﹐挂了特别车牌﹐马路上巡逻的宪兵们都有数﹐能够认得出来﹐看见车上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开着﹐又没有蒋纬国上校在旁边﹐自然要拦住了盘查。三舅开始怕给外祖父惹麻烦﹐所以不肯讲自己的身世。到了宪兵队总部﹐他真的怕了﹐只好老老实实报出自己的家门。宪兵队长官照着三舅给的电话号码一拨﹐就打到外祖父的家里。然后问蒋纬国上校是否在﹐没料到坐在外祖父对面的蒋纬国上校一听﹐就抓过电话答应﹐吓得宪兵队长跳起来﹐对着电话敬礼﹐报告一声没事没事﹐赶紧放下。
打过电话﹐宪兵队长擦掉头上的汗﹐且羞且恼﹐却又晓得陶家的公子不能轻易得罪﹐只得忍住脾气﹐把三舅好言教训一番﹐警告他不许再私自开家里来客的车子到处乱跑。却没罚三舅一块钱﹐其实就算要罚﹐三舅身上也没有﹐还得回家去取来才缴得上。然后那队长派了一个宪兵﹐开了那辆蒋纬国上校的特别吉普﹐连车子带三舅﹐一起送回外祖父家里。
一路上三舅又急又怕﹐心里七上八下﹐自知闯了大祸﹐外祖父如果晓得了﹐绝不会轻易饶过他。那个宪兵开车到了田吉营﹐并不敢进外祖父家门﹐或许是怕见到蒋纬国上校﹐便匆匆放下车子﹐自己先走了。三舅按住心跳﹐颠了脚尖﹐轻轻蹭进家门﹐顺着墙角边﹐偷眼看见客厅里面﹐外祖父和蒋纬国两个﹐还是原样坐在桌边﹐边饮茶边谈天﹐好像刚才并没有宪兵队打来电话﹐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三舅这才放下心来﹐走上楼去。他那天是没有挨外祖父骂﹐但是后来我的母亲知道了情况﹐却把三舅好骂了一顿﹐从此以后三舅再也不敢乱开家里客人的车子了。但据说我的父亲开了车去外祖父家﹐三舅还是忍不住要开出去过过瘾﹐好在父亲的车子不挂特别军用牌照﹐只有一张记者证﹐没有宪兵会拦住他了。
听舅舅们讲﹐到了台湾之后﹐蒋纬国将军还是经常到外祖父家里来谈天﹐讨论天下大事﹐而且仍旧一谈就是半天﹐兴致勃勃。不过那都是后话﹐我的母亲没有到台湾去﹐就不知道﹐也不会讲给我听了。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