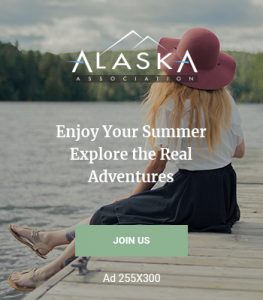几乎在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已经看熟了父母卧室墙上挂的一幅字画。上面是两棵高大的松树﹐长在一起。树很高﹐相当直﹐树干很长﹐伸入天空﹐只在树干顶端﹐才有一些枝叶﹐看起来有点奇怪。如此高大的树下面﹐站了两个小孩子﹐非常之小﹐几乎看不清脸面﹐一男一女﹐手拉着手。
到我四五岁﹐开始随父母认字之后﹐父亲就读那字画给我听。字画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字﹐竖排的﹐字体很有趣﹐好像小孩子手写一样﹐歪歪扭扭的﹐但是很好看。父亲读那八个大些的字﹕双松同根﹐百岁长青。左侧一行小些的字是﹕苏儒琴薰伉俪结婚之喜。署名是﹕丰子剀。
年纪再大一些﹐我就晓得丰子剀是谁了。
丰子剀是浙江桐乡人﹐同属嘉兴府﹐跟父亲算是同乡。父亲还曾很自豪地告诉我﹐他跟丰子剀先生读过同一所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丰子剀先生一九一九年从该校毕业﹐父亲则是一九三九年毕业﹐相隔二十年﹐还是校友。
不过直到进重庆中央大学读书之前﹐父亲并不认识丰子剀先生。关于父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的生活经历﹐我在另外一篇”天子门生”的文章里有详细记录﹐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因为本文专门是讲丰子剀先生的﹐所以必须做一个特别说明。

在收集丰子剀先生资料时﹐我发现国内有官方史料公然注明﹕儿子丰陈宝﹐女儿丰一吟﹐长期以来致力于其父著作的整理研究﹐然后通篇都是儿子丰陈宝﹐儿子丰陈宝地继续。这样的错误﹐让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既然能够了解到丰陈宝致力于研究其父著作﹐怎么可能不晓得那丰陈宝并非男身﹐而是女子呢﹖我把此误告诉给父亲﹐他忍不住大笑数秒钟﹐丰陈宝小姐跟我的父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同班三年。
或许有人将丰陈宝称做公子﹐所以让一些毫无文化常识的”文化人”把她当作是丰子剀先生的儿子了。殊不知﹐在中国旧式文人里﹐为表示尊重﹐是用公子和先生来称呼女士的。如尊称宋庆龄先生﹐难道也该把国母当作男子不成﹖有人或许怕被那些不学无术之辈误解﹐则用”女公子”一词﹐比如丰子剀先生的女公子丰陈宝﹐那就清楚许多了。
不知是什么道理﹐世人似乎特别与丰子剀先生的子女过不去。现在北京﹐有人将丰子剀先生之女丰陈宝小姐呼为儿子﹐五十年前重庆﹐也曾有人将丰子剀先生之子丰华瞻先生叫成小姐。抗战期间﹐重庆的《中央日报》曾发表一篇有关丰华瞻先生参加大学生学业竞赛获奖消息﹐内有”令媛”之语。那令媛是向对方小姐的恭敬之称﹐记者把丰华瞻先生当作丰子剀先生的女儿了。
当时在重庆﹐丰子剀先生夫妇读过那篇报道﹐大笑之后对儿子说﹕你最好写信请报馆更正一下﹐否则当心将来找不到媳妇了﹐据说丰华瞻先生果然给报馆写了信澄清。看来﹐中国一众所谓习文研史者﹐颇具粗心大意﹐不求甚解﹐随意编造之传统。四方读者﹐务必小心﹐白纸黑字印出之物﹐仍须三思﹐不可轻信。
事实上﹐丰子剀先生女公子丰陈宝﹐不仅在重庆中央大学与我的父亲母亲同班﹐而且与她自己的长兄丰华瞻先生同班。丰华瞻先生而且与父亲母亲是很要好的朋友﹐也许因此父母亲在上海结婚时﹐丰子剀先生会专门做一幅字画相赠。我们在家里﹐都是称丰华瞻先生为叔叔的。
抗战期间﹐丰子剀先生随任教的浙江大学﹐先迁广西宜山﹐又迁贵州遵义。一九四二年到达重庆﹐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其公子丰华瞻先生﹐后来也从遵义浙江大学转到重庆中央大学。同一年﹐父亲只身到重庆﹐从暨南大学转入中央大学读书。母亲也因外祖父一家到了重庆﹐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学到中央大学。这样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地方﹐都以转学身份﹐聚到重庆中央大学﹐显然是有缘份吧。
据我的三舅回忆﹐他在重庆南岸的小学毕业﹐要考中学。母亲鼓励他去投考南开中学﹐并且领了他去报名和参加考试。当时的南开中学﹐跟中央大学同在重庆沙坪坝。考试要连续两天﹐为节省三舅往返跑来的时间和精力﹐报名之后母亲决定不送三舅回南岸家中﹐就与同学丰陈宝小姐商量﹐借住丰子剀先生家过一两夜。
当时丰子恺先生家﹐在重庆小龙坎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塔附近的一片平地上,竹编的离笆墙﹐围住小院子,门口挂个小竹牌,上书”沙坪小屋”四字。房屋是竹架子外面涂石灰泥,屋里家具也大都是竹子做的。丰子恺先生在家里﹐穿一身中式褂裤,留着山羊胡,对母亲和三舅非常和气。三舅到在南开中学参加考试期间,在丰子恺先生家住了两天三夜。临走时候,丰先生还送给三舅一本自己的小漫画册。
又是缘份﹐丰陈宝小姐大学毕业之后﹐应聘到南开中学教英文﹐成了三舅的老师。然后抗战胜利﹐丰子剀先生回浙江杭州﹐父母亲回上海和南京﹐丰华瞻先生到美国留学﹐各奔东西﹐却未断联系。一九四九年后﹐丰子剀先生常年居住上海﹐父母则搬去了北京﹐丰华瞻先生虽在上海任教﹐但妻子在北京﹐所以经常北上﹐得与父母相聚。
我家与丰华瞻先生家那一段时间的往来历史﹐下面抄录丰华瞻先生的一篇文字。那是一九八八年﹐母亲去世十周年﹐我们三个子女编一本纪念册﹐写信给母亲的亲友﹐请求纪念文字﹐丰叔叔写了寄来的。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