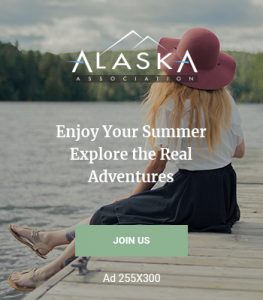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编者按)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我们在这里,美国亚利桑那州,有的人留下来了,有的人海归了,在时间和空间的交界点中,有很多分秒组成的故事,在太阳鸟亚省华人网中,我们看到张肇鸿,气如虹,文若,慧明,凤鸣,心水等很多老侨用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首先感谢他们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代移民的成长足迹。”太阳鸟”专栏作家汪静玉,根据生活在凤凰城女人的真实故事,撰写出了小说《凤囚凰》。
凤 囚 凰
汪静玉
2
我们刚刚开始交往,大规模的非典就突如其来的爆发了。每个人开始诚惶诚恐,生怕一不小心灾难就临到自己头上,空气传染病毒不仅让人出其不意,而且速度快得惊人。我不得不搬进姐姐华子留在驻马店的一套简易的小房间。房子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里面唯一醒目的是一张没有靠背的大床,这张硬邦邦的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卧室。
严格力骑车给我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他买了很多一次性口罩,我将这些口罩摆放在床头,每天定期戴上,连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早上醒来时不舍地扔到垃圾桶里,每扔掉一个心中的甜蜜就增加了一分。他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过来看看,每次过来都会带来新鲜的玩意。有人说烧药香能抗非典,于是我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令人欣慰的药香味道,后来他拿着药香仔细端详和辨别,发现这些其实都是艾条制作的,他又弄来几根陈年艾条,挂在门口,枯萎发黄的叶子在空气中兀自摇晃,像一些跳舞的小精灵,在这个恐怖的时刻这些小精灵给我内心带来令人无法想象的温暖和对未来无限美好的遐想。
他最后带来了电视机和影碟机,这个成为家里唯一的一个奢侈品让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在安装机器时,突然过来抱住我,抚摸我那从没被关注和触摸过的身体,我全身心颤抖地感受他的温暖,让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剧烈的心灵震撼,这种震撼从身体表面直抵心灵深处。
我们每天猫在家里卿卿我我,看电视,里面大多也是关于”非典”的报道。后来我们从这种例行的报道改为看影碟和听音乐, 我们在音乐或爱情片中找到了残忍现实生活的另一面,与我们现行的浪漫相比,一切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笼罩在我们身上的死亡阴影也渐行渐远…….
有一次,我们刚刚欣赏完一部影片,他坐起来掐灭手中的烟,说,要是”非典”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冒出这句话来。
他从床上坐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眼神有些诡异,他似乎不相信我不懂他话里的意思,又说道, 感谢这该死的”非典”,我不用每天上班,让我们有时间和机会天天呆在一起。
我还是没说话,他一定发现了我脸上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微微耸了耸肩,捂住嘴清了清嗓子,顺势将手伸过头来搂住我,他的嘴里呼出一股被隐藏得很深的酒气,他一边吻我的脖子,一边呼唤我的名字,他的表情和动作极其投入,使得我很快将所有不愉快的想法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种浪漫的日子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我们的美梦是被一只吊死在窗外的白色京巴狗唤醒的。透过窗户,这只狗惨烈的死状把我们吓得脸色惨白,一股股凉气从脚底直抽上来,我们拔不动脚,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截截烂肠子从血肉模糊的狗肚子里翻滚出来,鲜血汹涌地往外直喷,这只狗拼命地想把头抬起来,但它最后的努力落空后,它声嘶力竭地呜咽了一声,声音拉得很长,但很吃力,最后突然戛然而止。
我这才发现,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只有一个戴口罩的民警在执行公务,他正拿着一根钢管在拼命追赶一只黑毛狗。街头很多流浪狗在惶恐地奔跑逃窜,完全丧失了往日的悠闲和骄傲,它们慌乱的脚步代替了人的脚步,把整个街道震得咚咚直响。
这时,手机刺耳的铃声把我们同时吓了一跳,我们神经质地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由恐惧产生出来的恐慌,我们都盯着手机,像在盯一个快要引爆的炸弹,不知如何是好。
手机铃声执拗地响着,大有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严格力看了我一眼,无奈地拿起电话,是找他的,好像是某种命令式的任务,他嘴巴上拼命地服从,但脸色却越来越难看,完了把手机狠狠地砸在床上,烦躁地呢喃了一句,该死,为什么偏偏是我。然后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对我说,我可能很晚才能回来。说完他严肃地看着我,说,你不许出去,在这个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最安全。说完拎着鞋子出门了。
他加入到那个戴口罩的警察的行列了,他和另一个和他一样,成为这个街区打狗队的一员。他像是极力避免让我看到这一幕,每次快到这个街道的拐角处时就快速地躲闪开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他慌张缩回去的背影。他手上的金属管在空中很自如地划着圈。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天,每天他从战场上回来时,身上总是裹挟着一股血腥味和腐烂味混合在一起的奇怪臭味,这种味道足以让人窒息。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洗手间洗澡,他洗多久,我就站在那道反锁着的门外看多久,我浑身颤抖地听着里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尽管他浑身散发着肥皂香味地走出来,但我仍然觉得那味道刺鼻得让人无法忍受。
他尽量想保持原有的浪漫,所以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从一种残酷的血腥场面到温柔的风花雪月,要不动声色地挑战这两种极限,需要很大的耐力和修为,而他还是一个刚刚走出青春期的孩子。他对我做出的微笑让人哭笑不得,就像谁突然给他戴上了一个假面具。我极力回避了几天,这几天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其让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今天已经达到了极限。当他现在刚刚从洗手间里水淋淋地出来时,我劈头盖脸地问他,这几天你一共打死了几条狗?
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脸色立刻变得极为难看,就像一个他刻意隐藏了多少年的谎言一下子被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戳穿了一样。他也没想到我一直站在门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一丝让人无法察觉的冷酷感从他薄薄的嘴唇上一撇而过。他沉默了很久,终于说,我就是做个样子给他们看,那些狗其实也很可怜。
我往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便跑到房间去了,我在里面控制不住地大声叫嚷,你完全可以不做这个的,那些狗多可怜啊。
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这么激烈,他也对我大声嚷道,你懂什么?
接下来他打了个电话,借口有事,就穿上衣服出去了。然后一连两天都没有露面。这两天对我来说显得极为尴尬而煎熬,我明明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把他推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仔细反思因我的过失造成的这种局面,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茫然地看着窗外,外面的流浪狗少了很多。我趴在窗台上想,他还会不会再来?
第三天,他来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不声不响地搂在一起。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我们建立了一些宝贵的东西,但同时也在毁灭我们认为神圣的并一帆风顺的爱情。我们发展得太快了,我们很快认为对方理所当然地只属于彼此,而这种理所当然被看作是长久的且不容许有任何杂质。
几个月后,”非典”终于结束了,所有的出口解禁后,我像一只被囚禁了一个世纪的鸟儿,一下子冲出”牢笼”。我拼命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那些还没来得及消散的复杂气味还执拗地在上空盘旋,它好像在时刻暗示人们:这场世纪灾难并没有走远。街上人来人往,人们脸上挂着的惊喜之色,他们大声地和身边的陌生人打招呼。我骑着自行车在街区打圈,像一只撒欢的小狗。
就在这个周末,严格力带我拜见了他的父母,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此正式确定了。
作者简介:汪静玉,笔名王一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生,14岁开始发表作品,17岁独自闯荡大江南北,18岁保送武汉大学中文系,200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班。曾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家》、《芙蓉》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次被选刊转载和选入选本并多次获奖。著有诗集《青春的馈赠》、小说集《爱是绿叶》、《邂逅天堂的后窗》,出版长篇小说《天堂眼》、《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等9本书,其中《天堂眼》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2009年赴美。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