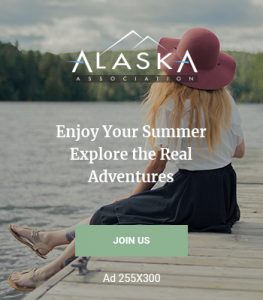凡事沾了”野”字就平添了几分粗旷,原始和神秘。
滑雪场里没有野雪。那里的雪道有标识,有界线,由重型机械清理和平整,滑雪场还有救护人员,万一有了闪失,雪上摩托会来照应。当然,这些服务都包括在几十,上百美元一张的缆车票里。
野山旷谷里才有野雪。那里人迹稀少,这其实是一种最好的安全保障;那里也没有缆车,也就不可能有故障。滑野雪的路数就是身背滑雪板,咬牙喘气,苦撑一天,登临山顶之后,喝几口西北风,然后踏上滑雪板,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高山速降,一路神仙,重返尘世。滑野雪虽然刺激,但一天只能玩一趟。
滑野雪的设备同在滑雪场使用的设备不一样。首先,雪板和固定器(Bindings)一定要轻。不然背在身上登山,走不了两英里就歇菜了。一付登山滑雪板和固定器的重量加在一起不到十磅。雪板下边还要能安装用于爬坡的冰爪或摩擦条(Skins)。这样在不太陡的雪坡上可以踏着雪板上坡。其实踏雪板上坡并不比背雪板上坡省力,但踏滑雪板上坡的安全系数大增。大雪之后,坡面上的冰缝和窄沟被浮雪掩盖,徒步登山就有可能失足掉进去。如果冰缝和沟太深,掉进去爬不出来了,那就玩完了。但如果踏着滑雪板登山,万一掉进冰缝和沟里,有可能被长长的滑雪板卡住,说不定就能捡条命。
第二,滑雪靴也不同,滑野雪需要专门的登山/滑雪两用靴。既要像登山靴那样鞋底耐磨,要能带冰爪;还要像滑雪靴那样能将脚腕和脚掌约束住,以便对付滑雪时前后左右的冲击力。这种滑雪靴说是两用,其实论登山比不上登山靴;论滑雪比不上滑雪靴,就是一个折中的”两不像”。
器材设备是滑野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除了吃饱了撑的之外,滑野雪的动机可以多种多样。其中一条是空灵,静谧的雪山有无限的诱惑力。
一次,在科罗拉多州海拔4349米的Grays峰,早上五点半我就摸黑背着雪板上山了。一路大风,新雪松软,深一脚,浅一脚,几次差点让风刮倒。六个小时之后,攀登到距离峰顶还有400米左右的高度。这里的坡面都是裸露的石块,不可能滑雪。于是我将雪板插在地上,徒手上山。这样上山的速度大增。拼死拼活到了山顶,手已经冻麻了,脸也让风刮得生疼。胡乱拍了几张相片就掉头往回跑。想快点穿上滑雪板”飞身下山”,享受那”极乐的二十分钟”。不料原路下来后却找不到滑雪板了。驴转磨似的搜寻了足有10分钟,才发现原来插在石头缝里的滑雪板被风刮倒了。

作者背着滑雪板在进山的路上。背包也是特殊的,能在侧面挂两只滑雪板。

科罗拉多州Grays峰的冬景—-摄于半山腰。
下山滑行时不敢得意忘形。不但要绕开山沟和陡坡,还要小心藏在积雪下的尖石。尖石不但能划坏雪板,还可能把人绊个大跟斗。在山腰,有一处平台,没有障碍物,雪况看上去很好,我不由加快了速度。孰不知这里原本是一个小山谷,风将积雪都填到了这里,松软的积雪把地表变成了平面。我冲进去后,雪板一下陷了下去,但整个身体还在向前冲,于是人飞将出去,摔了个嘴啃雪。整个脑袋都扎进了雪里。好在雪地松软,摔不坏。但爬出来可不容易。四周的雪都是软的,没有支撑点,只能先卸下雪板,然后抱着雪板滚出这片松软的雪地。
出这一片”雪潭”真是不容易,气都快喘不上来了。然后坐定把钻到脖子里,耳朵里,靴子里和袖口里的雪清理干净。这时我才得以享受一下高原雪山的冷艳景色。在不知不觉之间,风已经远去,我将滑雪服的帽子脱下来,耳边竟然没有一丝声音。一侧脸颊上感觉到一丝暖意,那是面对太阳的一边;另一侧,依然阴冷如常。摘下墨镜,那冬日午后的阳光依然刺眼,深蓝色的天穹向四周伸展至无限。天上没有一片云彩,空气中没有一分杂质。近处的白雪在熠熠闪烁,那些躲在阴影中的雪面依旧深不可测。远处的沟壑,隆起的山脊,都透明般的清晰,山下那条冰封的小河蜿蜒弯向山外厖山外有路,有车,有人气,是社会。这里无路,无音,无世俗,是自然。
滑雪下山就是快,20多分钟就到了平地。上山可是奋斗了七个小时。回家一看,雪板下还是被石头划出了不少硬伤。
还有一次带一位朋友进山。走了大半程,他死活不走了,非要下山。于是我自己先滑下来,他只能走下来。下山后,我开车回旅馆洗澡,吃饭。两个半小时后再回山口接他,他还没出来呢。我这滑雪的”机械化”部队就是快捷。
我滑野雪的最高纪录是在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5500米的一号营地。那是六月下旬,虽然刚刚下了雪,但白天气温升高,积雪部分融化,晚上又冻成冰。在冰坡上必须用长滑雪板才能挂住。我万里迢迢从美国带去的滑雪板太短。在坡上很难刹住。那时的航空公司都允许两件托运行李,每件72磅。即使如此,为了登山滑雪,我还得想招额外托运行李。
还有用直升机将滑雪者带上山,然后滑雪下山的玩法。这样活动半径更大,能在一天内上到5000甚至6000米级的山峰。不过,背滑雪板上山最原始,也最牛。
2012年4月26日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