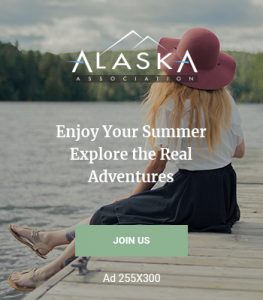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快餐文化的流行,说书说文化也成了流行的文化了,而”文化”一词不知不觉被形形色色的人无数次地滥用。各种媒体自然而然地跟风,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多媒体, ”文化”这个词的出现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似乎有暴涨的趋势。什么”文化产业”,”文化品牌”,”饮食文化”,”茶文化”,”文化”,”文化旅游”,”文化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校园文化”,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令人叹为观止。读了几天晚报,就说是懂文学了;能哼几句流行歌曲,自然就算是会音乐了。就连那些五音不全的巨星天后和俗不可耐的贪官污吏只要跟”文化事业”沾一星半点的光便像打了鸡血吞了大力丸似的成了”文化(名)人”或是”大师”,到处留下”墨宝”,到处给人指点迷津。更不用说那些”常凯申”、 ”孟鸠斯”【注1】之流、名真货不实的专家教授是如何顶着”文化”的招牌粉墨登场、欺世盗名了。
我们谈的”文化”,特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科教文方面的财富。这里不是谈”读书认字学文化”的扫盲,也不谈小团体的氛围常规,如”公司文化”。通常,人们对文化本身的认识存在相当大的误区。人们总以为顶着”教授”、”专家”、”博士”、”硕士”、”某某长/官”光环的人就是有文化。实际上,有地位权势、学位、头衔、金钱、有专业的知识技等等能虽然可能与狭义的文化范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代表有文化。要不然的话,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岂不都得让那些个博士、教授和官员来担当了?所以,不能把懂几国文字,有什么学位作为是否有文化的标记,更不能把广大人民看做没文化的中小学生或是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偏见甚至愚蠢。
一些由学者主讲的讲座总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如易中天的品《三国》和 康震《王安石》。扪心自问,大家整天又是忙工作,又是忙炒股,又是倒弄房地产,有谁真能定下心来读几本书,更遑论做学问想问题了。于丹的《论语》讲座是不错的普及型文化讲座,据说很受欢迎。要建一座房子不容易,但要挑些毛病或是推到它虽然要有一定的气力,但毕竟要容易许多。写书做讲座与看书听讲座的关系也是如此。
北京晚报前不久刊登了作者苗连贵的批评文章。苗先生指出:于丹将《客中行》一诗中的”琥珀(po”,读成hǔ bo;将《从军行》诗中的”吐谷(yu)浑”,读成tǔ gǔ h鷑厖这两首诗都未超出中学教材范畴。《于丹趣品人生》读来赏心悦目,但读到《琴之趣》中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发现作者有一点小小的疏漏:误以伯牙为俞伯牙了。譬如,第151页”俞伯牙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超的琴艺呢?”第152页,”俞伯牙身处荒岛,不知如何度日”。第153页,”俞伯牙向’空’中学’移情”’等多处。伯牙非俞伯牙也,历史上并无俞伯牙其人。伯牙姓伯名牙,与周武王时誓不食周粟的伯夷姓伯名夷、秦穆公时期相马的伯乐姓伯名乐一样。在中国上古时期,”伯”是一个很普通的姓。《吕氏春秋 本味》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东汉高诱对之注解时明确指出:”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荀子 劝学篇》说:”昔日觚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伯牙是当时的古琴名师,技艺高妙,马为听琴忘了吃草料。《琴操》、《乐府题解》则记有伯牙向连成先生学琴的故事。以上文献所述,皆直指伯牙。现代的《词源》也注曰:”伯姓牙名”。同样是讲故事,人们对著名文化学者和普通人的期待与渴求是完全不同的。学者讲得精妙,理所应当,如果讲得像温吞水,甚至出现一点点疏漏,都会受到众人指摘。
于丹的讲座毕竟是言而有物,讲了故事,也讲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她的讲座面向老百姓,基本上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作为一个学者,难免有一定的偏见,有时甚至是以偏概全,失之公允。比如把”三八就是二十三”的命题说成是中华文化的精深道理就很难令人信服。如果牺牲真理而对一个街头混混的实行”绥靖”,那么,青面兽杨志为捍卫尊严而当街宰了无赖牛二难道就不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吗?如果真理可以随便牺牲,尊严可以随便丢弃,那么,”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攘外必先安内”,”绝对不抵抗”,”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等等都可以脱掉卖国主义的帽子,堂而皇之地戴上中华文化精髓的桂冠?!胯下忍辱韬光养晦是为了来日横扫天下大展宏图,关键时刻敢于亮剑以捍卫真理、捍卫尊严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
于丹在演讲中用实例来说明东西方宗教观念,伦理秩序的不同。她举例说,西方的教堂是垂直式的单体建筑,例如哥特式的教堂高耸向上,向天空伸延,意味着向天顶的膜拜。可她怎么就对中国高耸入云的塔视而不见呢?!她还说中国人的建筑是向水平延伸,是群体的建筑,呈现出俯拜于大地的秩序。难道她就不知道所谓的高楼大厦群仅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巍峨的阿房宫、大雁塔、长城、祈年殿都是”俯拜于大地的秩序”?再说了,”西方的教堂是垂直式的单体建筑”,难道中国的庙宇,道观就只是”向水平延伸”而已的小玩意?拿西方的精神堡垒教堂来与中国同时期的乡下民居进行对比,或者拿印度的泰姬陵和苏格兰的羊圈进行对比,才会得出这么无聊的结论。试问,文化研究的学术尊严何在?
于丹教授在讲到”向艺术借鉴风格”时说,中国文学的特质是”写意”的。于丹以莎士比亚同时期的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昆曲《牡丹亭》为蓝本,用汤显祖剧本里朦胧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太守的千金小姐杜丽娘在梦中遇到俊逸书生柳梦梅的情景,醒来后要去”寻梦”,并因梦而亡又因梦而生。”朦胧诗一般的语言”在西方的文学家的作品中也很多。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以”梦”来做引子。’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 难道西方文学的特质只是”写实”的?
以东方围棋举例,于丹教授认为,中国人发明的围棋,不同于西洋棋,没有国王,没有王后。每枚棋子都是平民的身份。下棋就是占边占角,使布局足够大,完成整体的布局,形成气象万千的布局,在大格局上取胜,而不是争一口气的小布局。中国人下棋,不叫博弈,叫守盘。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是不称霸的,不需要此消彼长的,是互济共长的。东方人的生活态度是圆润从容的。【注2】
这么一来,中国象棋的将帅士相车马炮兵卒以及西方的九方格游戏等博弈似乎统统没有了”文化”的资格。至于 ”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是不称霸的”的结论更是莫名其妙。当下中国确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美其名曰”韬光养晦”,但这并不等于要把春秋五霸乃至”缓称霸”的朱元璋等一干盖世霸主在史册中随便一笔勾销呀。
”东方人”的生活态度是”圆润从容”的?谁是”东方人”?日本人?朝鲜人?中东的阿拉伯人?蒙古人?越南人?中国人?还是专指于教授生活小圈子里的人?且不说外国人,就咱中国人而言,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圆润”富士康的工人”从容”吗?到北京的大街上看看,在上下班的匆匆人群里,有几个是”圆润从容”的?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态度。亚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将亚洲人界定为”东方人”大致不错。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二居住在亚洲。试问,这近40亿的人中有多少人的生活可以称得上”圆润从容”?
于丹教授还认为,太极图的黑白两色图形蕴含着高深的辩证法;中国人的”太极拳”中有高级的智慧,当遇到外在的打击时,不硬碰撞,以柔绕过,将对方引入到空落之中。【注2】 这里谈到了中国的武术文化。太极拳的”高级智慧”体现了以柔克刚的理念,这只是太极拳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太极拳以刚制胜的另一方面:”会不会?金刚三倒锥!”练过或看过陈式太极拳的人大都不会天真幼稚到把太极拳当幼儿园或敬老院的广播体操的。除了太极拳,中国的武术门类千千万万。就刚猛劲健而言,少林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没见过武僧的表演不要紧,看看《少林寺》一类的武侠影视或书籍也行。再不行,看过或听过CCTV春晚的武术表演或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武术表演吧。太极图中的黑白二鱼正是体现了刚柔并济、阴阳平衡的”高级智慧”,而绝不是只阴不阳或只阳不阴的阴阳失调。
常识告诉我们,相对对等的比较才有意义。搞文化学术研究,不能拿张家的枣子跟李家的BBQ相比,拿Smith家的领带跟王家的草鞋相比,然后信口开河地谈观点谈结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本身既不是很好的学术态度,也不是对读者听众应有的尊重。其谬大矣。
这种思维上的逻辑紊乱在于丹的演讲中随处可见。比如:西方人的舞蹈是托体的、高高向上的;中国人的舞蹈和戏剧演出是跑圆场、卧鱼式的,是圆润的。西方人不仅国旗上有苍鹰,西方的诗歌也是歌唱单体的、雄健的苍鹰的;而中国的诗歌是讴歌群鸟,李白杜甫的诗歌里写的是小鸟、群鸟,山花和群花;现在中国人唱的歌也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不是唱”我是一只大大的鹰”,等等,等等。
”高高向上”的芭蕾舞是西方舞蹈的一方面,而与大地亲密接触的踏踏舞和街舞是另一方面。在中国,同样有”高高向上”的舞龙和高跷。但我始终不明白什么艺术才叫”托体的”、”跑圆场”和”卧鱼式”的!至于”单体”、”群体”之说更不知是根据什么统计数字或研究结果。西方的图腾可以是鹰,怎不拿来和中国的凤来比?。谁说西方诗人不写小鸟?西方诗人中写小花,小草,小动物的千千万万。读读雪莱【英】笔下的云雀吧:
Hail to thee, blithe spirit!
Bird thou never wert,
That from heaven, or near it,
Pourest thy full heart
In profuse strains of unpremeditated art.
Higher still and higher
From the earth thou springest
Like a cloud of fire;
The blue deep thou wingest,
And singing still dost soar, and soaring ever singest.
In the golden lightning
Of the setting sun,
O’er which clouds are brightening,
Thou dost float and run
Like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 . . . . .
多美的诗篇啊!浪漫主义诗人真是出手不凡!没读过这《云雀颂》不要紧,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吧?那是编入中国小学课本的。依照于丹教授的说法,高尔基写的海燕到底是”单体”,还是”群体”?如果没法欣赏那些优美的诗篇,听听舒伯特的《听、听、云雀!》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呀。再不行,看看俄罗斯的《天鹅湖》和中国傣族的《孔雀舞》总可以吧。录像也行呀。
中国诗人只会写小鸟小花?笑话!看看中国古代诗人们的作品吧。李白心中的鹰清高飘逸:
八月边风高,胡鹰白锦毛。
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
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
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云霄万里高。
杜甫笔下的鹰杀气森森:”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白居易描写的鹰是威风八面的:”。。。。。下鞲随指顾。百掷无一遗。 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
柳宗元笔下的鹰则是横空出世的大侠了: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清代诗人陈维崧有词一阙《醉落魄。咏鹰》,也相当精彩:
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
秋空一碧无今古,
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
老来猛气还轩举。
人间多少闲狐兔,
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中国人的诗歌既有婉约细腻的,又有豪迈雄浑的。这些咏鹰的诗词至今读起来,照样让有骨气、有良知、有正常思辨能力的人们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自小就钦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英雄人物:堂堂正正,阳刚伟岸。中国诗人歌颂苍鹰,猛虎,骏马,乃至腾云驾雾的龙的作品无数,那些瑰丽的篇章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就”谈文化”而言,如果只是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其实无伤大雅,也许还有助于大众对文化的关注和讨论;如果是由于偏见,那就离真理更远了,因为谬误的积淀不能构成正确;如果是固执己见、不肯学习,那就是谬种流传,害己误人;如果是别有用心,故意给祖国文化抹黑,那就是欺世盗名,罪不容诛了。
我觉得关于文化的讨论和报道挺有意思,看了之后就转给我的几个学生看。他们都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年轻人。没两天便收到了尧儿的回邮。她的看法令人思考:
”。。。。。。我觉得这些学者最大的问题就是盲人摸象,或者喜欢非黑即白,每个人都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异端。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那个是能用一个故事一个演讲甚至一篇论文说得清楚,或者说得全面的东西吗?于丹的话虽然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的确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一面。至于这是好是坏,以及是不是”精”的,那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实行全民民主了,大家都来投票决定,那么或许才能算是有个定论。于丹说话可以少代表一些别人(例强调这是她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批判她的人可以少极端一些(即不要全盘否定,而是指出她的看法不够全面)。
当然,我觉得要是要求这些文学家们理性地谈文化有些不太实际,毕竟那样会让争执少很多,大家各自发的paper就都少了。
至于于丹讲话本身。。。。。。私以为有点华而不实。例如:于丹教授说,西方人强调严谨的结构,把情感的产生归纳于头脑思维的结果。中国人是用心灵生活的,用五脏六腑来表达感情,用”肺腑之言” 、”肝肠寸断”、”满腹经纶” 、”肠子都悔青了”等词语来描述情感,是解构的。于丹教授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模糊和解构的,虽有缺陷,但有其长处。单看这一段就很有取样偏见,用来唬一下英文不好的中国人是可以的,但是英文里不光是用brain思考,各种 heartbreaking, gut feeling, got guts, bilious… 将感情和性情跟五脏六腑联系起来的也是有的。
。。。。。。关于”鸟”的命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实很能说明中国人的看法。不但推崇”鸿鹄?贬低了”燕雀”,跟于丹说的截然相反啊。尤其是人们对文化的误区,迷信所谓的专家的光环这一点上,我觉得这是关键。有于丹的讲座不是一个问题,毕竟如你所说,她普及了一些知识和她个人的看法,让大家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但是如果因为于丹现在的地位而导致听众只听她的讲座,甚至把她说得所有话都当成真理,这就成了真正的问题。所以说症结不在”专家”棗总是会有一部分专家的意见被另外一部分反对,孰对孰错未必总能理清,而是在于大众能否做到兼听则明,而不是一味盲从偶像。”
纵观当今世上,瓦釜雷鸣而金钟毁弃。把书教好、把自己专业的学问做好的教授也许一生”躬耕于陇亩之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某些”文人学者”、”教授专家”偏不甘寂寞,剽窃作假,走穴作秀,贿官买爵,或以奇谈怪论哗众取宠,或数典忘祖卖身求荣。数黄道黑,头头是道;坐谈立论,无人可及。若论治学教化,一无所长;安邦定国,百无一策;若论歪门邪道,却是不择手段,全无羞耻,花样迭出,唯名利是图。但几年下来,发迹的发迹,发财的发财;虽学问本事未见长,名利地位却丰收。相比之下,于丹教授的讲座还是不错的。平日里,大家听听相声评弹、看看小品戏剧,不也可以愉悦心情,感悟世态吗?
无论是听稚童讲故事还是听老农闲话茶桑,只要静下心来倾听,都会获益匪浅,更何况是听CCTV的《百家讲坛》节目中于丹等大腕教授令人回味推敲的讲座了。对于丹教授为普及文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我始终是心怀感谢的,因为她的讲座总能引起我很多有关文化方面的、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种种思考,从而鞭策自己、警醒自己。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精神财富面前,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面前,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贝的小学生,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偶尔从肺腑中发出几声”啊,大海,好美啊!”如此而已。。。。。。
【注1】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教授所著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2008年)原來只有兩章,分別是關於中國大陸及港台學者和俄羅斯及蘇聯學者的研究,後來王奇教授加入關於西方學者的第三章。其中多處錯譯人名、期刊、書名、出版地和出版社,包括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常凯申”。
2002年初因涉嫌学术剽窃而引起社会关注的北大博导王铭铭教授曾经组织编译过一套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丛书,其中有吉登斯的《民族棗国家与暴力》(胡宗泽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英文原著中引用了孟子的经典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在根据英文版翻译而成的该书中,居然翻译成了:”门修斯说,太阳之下都是王的民厖”。这学术水准令人匪夷所思。
复旦大学的学术网站【正来学堂】在2006年五月刊发了同济大学哲学系陆兴华教授的研究文章,把词人毛泽东一夜之间变成昆仑山:”。。。。。。(德国学者)施米特引用了中国诗人昆仑的诗句来展望这种世界革命或战斗下的真正的政治的斗争和和平:把革命和战斗的火种当礼物,一把送给欧罗巴,一把送给美利坚,一把留给中国自己,这样和平才会来主宰世界。[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相比之下,像大卫、刘谦之辈玩的魔术简直就是小儿科了。
许多人也许在小学时候就熟读过毛泽东的著名词篇《念奴娇 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注2】 见文若:《”三八就是二十三” – 听于丹教授的专题演讲》。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