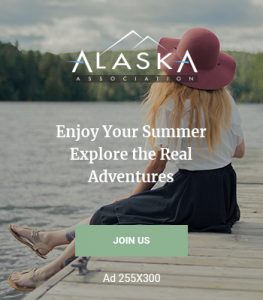郎朗2011年的首场演奏会在凤凰城举行。在安妮姐姐的安排下,我不仅有一顿昂贵的贵宾餐,还有和郎朗吃饭,见面聊天的机会。原本计划好好做一个专访,可是厖
Henry 是从事高科技的台湾商人,他高价投得了郎朗演奏会的贵宾餐和贵宾席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只有六个席位的贵宾活动。贵宾餐厅设在郎朗演奏厅的后台,一个小房间装饰的很漂亮。我也不知道这昂贵的菜能吃出个什么来。照例第一个是沙拉。我看着盘子里放着色彩各异的长得奇怪的”草”就硬着头皮吃吧。然后,出来的是当天的主厨,他来介绍每种”草’的出处,这些东西在凤凰城当地是绝对没有的,他们来自哪个农场,几点到到凤凰城,被分发到哪几家昂贵的餐厅。为什么这么搭配。我一边听,一边继续嚼草。不过有几种草的香味真的很特别。味道就不说了,我向来对新美食没有太大的兴趣。就如领导说的,每次让我去新餐厅尝菜我都跟上刑场似的。大厨说红酒是从哪个特别的渠道来的,我也忘了,反正他们几个都在美美的品尝,因为我要的就是白水,还不要冰厖第二道菜是长的很像中国混沌的东西,里面就是包着什么特别的cheese,还有肉类,保证我们吃的时候温度多少之类的高难度的烹调技术。据说是意大利和日本料理的做法,还有一个东坡肘子的主菜,还有甜品之类的。因为知道今天的贵宾都是亚洲人,大厨特地做了中西结合的美食。据说Henry一家都是美食家,非常会品菜。他们到世界旅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尝尽美食,而且预言给我们做菜的主厨在7年左右必成大器。他们刚从亚洲回来,在日本吃了个什么东西,一个人1000美金。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面对这样的好菜,真是暴殄天物。但是有一点是学到了,原来贵宾之所以贵,都贵在稀少的原料和周到的服务。我是个粗人,还是比较想念老四川的水煮鱼。
郎朗的演出当然精彩,对于我这样的外行真不敢评价。唯一改变采访计划的就是和他在一起的经历。和一堆我们爸妈年纪一样的成功人士在一起,还有一个人跟我和郎朗谈起了孩子教育之类的话题,我们俩互相交换了眼神,什么也没说出来。郎朗埋头苦吃,偶尔礼貌的开些玩笑,还跟一些华人朋友大声称兄道弟,很适应应酬的样子。唯一会定定眼神的时候就是手机。看短信,发短信,微笑。我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名利双收的大孩子很可怜,因为我太能感觉这样环境中的苦痛。我和他一样,在老华侨圈子里混,参加任何活动我都是最年轻的,我也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唯一管用的就是职业性的微笑。用眼睛看,记录下自己应该记录的东西。很多人找他拍照,签名,每当看到他有点时间的时候,都不忍心去问那些无聊的问题。他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说是,他说他比我幸运,他指指他妈妈,我就笑,好像他问我的的问题不比我问他的少。我放弃了自己的专访计划,就是希望多给点他看手机和朋友聊天的时间,那时我不想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记者,就当一个爱听音乐,爱看到有才华年轻人的路人好了。没有采访,我也过的很开心,照样写文章交差,我跟郎朗和阿姨说再见的时候就是祝愿他们美国之行平安,弹得好不好都没关系了,开心就好。
打开微信扫一扫
点击右上角分享
此文章到朋友圈